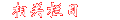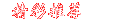
- 悼念晋绥老前辈毛大风叔叔(07月20日)
- 一位百岁老红军的襟怀(07月08日)
- 一场别开生面的视频签约(04月30日)
- 林炎志:继续做好铺路石(04月27日)
- 黄河古渡黑峪口 “两弹一星”晋绥情(04月08日)
- 六百英灵—远方山中的牵挂(04月02日)
- 怀念老红军张文阿姨(03月29日)
- 想起贺老总在晋绥(03月21日)
- 虎年初春晋绥情(02月20日)
- 怀念“四八”烈士后代—秦新华大姐(02月16日)
十年生死两茫茫--怀念我的妈妈冯佩璋(二)
发布日期:2017-04-28 11:47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作者:任洪凌
任洪凌
在汾阳铭义中学这所革命摇篮学习,妈妈接受了先进的革命理念和思想,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不少热血青年投奔延安。爸爸和妈妈先是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爸爸还在北平参加“12.9”学生运动,被抓进监狱。出狱后很快到了延安。妈妈在得知爸爸去了延安的消息后,马上放弃学业,邀约了几个同学,准备去延安。当时妈妈的学业就快要结束,已经进入实习阶段。她的老师是一位加拿大人,力劝她留下来完成学业。可是妈妈决心已定,那位老师表示非常遗憾。
从胶东到陕北,路途遥远,跋山涉水,尤其是要横渡黄河。其艰难险阻可想而知。听妈妈讲,当时他们两男两女四位同学,在黄河边搞了一条老乡的羊皮筏子,就这样四个人冒着被河水吞噬的危险,坐在羊皮筏子上,穿过波涛汹涌的黄河,来到陕北。
2000年,我到兰州参加一个会议。会议结束后主办方组织我们坐羊皮筏子在黄河上漂了一小段。我们坐的还是比较大的,就是起码四张羊皮吹涨后用木头连接在一起的。黄河的水流量在几十年后已经降低了不少,旁边还有救生人员,可是我仍然感到惊心动魄,不断的大呼小叫。可想而知,当年我的妈妈横渡黄河投奔延安,来到我的爸爸身边,需要多么大的勇气,付出了多少艰辛?
妈妈到延安后,就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她是四期的学员。后来还进入过马列学院等深造。由于她的医学专业背景,除了在报社工作过之外,还先后在兴县和临汾等医院担任过院长职务。多年前一次遇到一位同龄人,他说:“你知道吗?我还是你妈妈接生下来的。”后来我去问过妈妈,她说,我那时经常给人接生,除了革命战友,还有当地老乡。到底接了多少接了谁,她也不记得了。

1
在妈妈92年的人生旅程中,伴随着数不清的苦难和艰辛。可是她都凭借着自己坚强乐观积极向上的信念,迈过了一道一道看似无法逾越的坎儿。每一道坎儿都足以摧毁一个人的精神和肉体:
童年家境贫困,早年父母双亡。可是她以自己的顽强精神和聪明才智,一直念到大学,成为我党一名知识型的女干部。她最后的职称是主任护师,正教授级别,也是护士专业里的最高职称。在这个领域里可谓凤毛麟角。
来到延安,后来调到兴县晋绥分局,住在黄河边上的黑峪口。她又要工作又要带孩子。那时老区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生了孩子,最好的补品就是自己在窑洞后面种的新鲜番茄,外加小米大枣粥。如果能够养一只羊,在奶水不够的情况下,每天给孩子挤一点羊奶来吃,那就是母子的天堂了。
妈妈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儿,取名小波。小波聪明伶俐,长到6、7岁就知道为家里分担一点困难了。一天小波和同伴来到黄河边上,脱下鞋袜,去打捞河面飘下来的一些树木,准备拿回家当柴烧。不小心失足落水,被滔滔河水卷走。妈妈赶到河边,只见到小波留在河边孤零零的一双鞋子。那段时间,妈妈每天都会跑到黄河边上去,对着无情的黄水撕心裂肺的呼喊“小波--小波--”悲惨的呼喊在村子里回响,令所有人心痛不已。村里的老人至今都还记得。

我的大哥小波(左)和段云叔叔三女儿段晓峤1948年摄于兴县北坡,这是大哥身前唯一的一张照片。
可是噩梦并没有结束,妈妈的第二个孩子--一个大眼睛的漂亮女孩儿,身体结实,黑眼珠整天滴溜溜的转,性格就像男孩子,成天跑来跑去一刻也不停歇。于是妈妈给她取名铁蛋。一来取其性格像男孩子,二来名字粗俗些也好带。可是铁蛋长到一两岁的时候,不幸因感冒而引发肺炎,本来已经有所好转,结果一次在窑洞外撒尿着凉,病情加重,不幸去世。那时连磺胺都没有,以现在的条件,一个小儿肺炎不会就这么轻易丢掉性命的。
一连两个孩子夭折,给妈妈带来的打击可想而知。可是妈妈还要忙着工作,忙着去为战友和老乡接生......
无论时光如何流逝,她能改变很多,却抹不去人们对家乡对童年的记忆。在最后的日子里,妈妈大脑萎缩,记忆力减退,很多事情忘记了,很多人也不认识了。可是只要我们问起相子垣村,她马上就两眼发出明亮的光芒:“相子垣?那是我家嘛。”于是我的记忆也会随着她遥远的回忆,飞越千山万水,来到黄土高原,来到那个小山村,来到那个深深的沟壑旁,来到那个也许已经被吞没的土窑洞,来到那个暖暖的土炕上……
2015年8月,时隔半个世纪,我再次来到汾阳,来到妈妈的老家相子垣村。这回条件好了,太原的亲戚开着车。从汾阳城出来,虽然都是乡村土路,但是仿佛比我们当年走过的路要好多了。一路之上还是有一点荒凉之感,快到村子的时候,两旁树木多了起来。忽然汽车往左一拐,前方出现一堵红砖墙,胡乱涂抹的白石灰上书“相子垣”三个红色大字,虽然字迹部分脱落有些斑驳,但我还是远远就认出来了,我手指前方大喊一声“相子垣!”车刚停稳,我跳下来就跑过去,背靠墙壁,紧挨着相子垣几个大字,拍照,拍照。“相子垣”几个字那么普通,那么土气,可我心里却仿佛见到故人般开心,也仿佛寻觅到最亲的亲人般激动。背靠土墙,好像依偎着我亲爱的妈妈般心中无限温暖和甜蜜。

我在相子垣几个大字前留影

进村小路
我的大舅早已过世,在老乡的带领下,我来到妈妈窑洞的旧址,原先的窑洞早就没有了,现在是村子里的老乡后来盖的。完全找不到当年记忆里的样子了。我怅然若失,只好在人家房子的后边拍了几张。他们家的房顶是个平台,我站上去瞭望四周,想象着当年站在妈妈家窑洞顶上的情景。回想着妈妈92年的人生点点滴滴。

妈妈家窑洞旧址,已经盖起了新的房屋。
2011年3月28日,农历2月24,清明前夕,我和我的弟弟弟媳们把妈妈的骨灰迁到爸爸身旁,在我的博客里是这样记述的:“昨天终于完成了一件大事--把妈妈从磨盘山接到真武山公墓,与爸爸合葬在一起了。我不顾腰疼,亲自抱起妈妈,一条腿跪下去,把妈妈小心的放在爸爸身边,然后封盖合墓。我轻声地说:“妈妈,现在好了,你和爸爸又在一起了。你们这对60多年的患难夫妻,现在又可以相互照顾,相互体贴,永远也不会分开了……墓旁的柏树已经长得很高,那棵歪脖子桃树上的桃花也差不多凋谢了。我们点上蜡,供上香......我想,我们和爸爸妈妈的这种至亲的血缘亲情,已经建立好了新的联接--那是一种深入血液深入骨髓深入灵魂世代相传的依恋关系,无论天上人间,永远相伴。”(完)
冯佩璋:1915年出生于山西汾阳相子垣村,1936年加入民族先锋队。1937年4月,毅然放弃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的学习,来到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队、军事队,任女生大队副指导员。1938年入马列主义学院三期学习。1940年后历任《晋绥日报》材料编辑、兴县医院院长、临汾县医院院长。1950年南下后任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成都市妇产科医院院长、党支部书记、主任护师。1983年离休,2007年10月25日去世,终年92岁。
作者:任洪凌,冯佩璋之女,1949年出生于山西兴县。主任编辑,曾任《大众健康报》常务副总编、成都市健康教育所副所长,《成都晚报》责任编辑、专刊编辑。2004年退休。
照片提供:任洪凌
本站编辑:林 子
主办: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晋ICP备15001143号-1
Copyright Shanxi Jinsui Culture Education &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9号院国投财富广场4号楼313/314 邮编:100073 电话:010-63395639/63395661 邮箱:sxjs9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