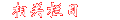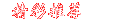
- 悼念晋绥老前辈毛大风叔叔(07月20日)
- 一位百岁老红军的襟怀(07月08日)
- 一场别开生面的视频签约(04月30日)
- 林炎志:继续做好铺路石(04月27日)
- 黄河古渡黑峪口 “两弹一星”晋绥情(04月08日)
- 六百英灵—远方山中的牵挂(04月02日)
- 怀念老红军张文阿姨(03月29日)
- 想起贺老总在晋绥(03月21日)
- 虎年初春晋绥情(02月20日)
- 怀念“四八”烈士后代—秦新华大姐(02月16日)
悲壮的黄树坪之战 作者端阳生
发布日期:2016-06-06 11:10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作者:端阳生
作者 端阳生
从1980年开展党史、军史资料征集工作以来, 我一直留意着1944年10月间偏关县黄树坪战斗的图片、资料、回忆文章问世。在那次遭遇战中, 除司令员姚喆同志回后方汇报工作不在, 凡在前方的绥蒙党、政、军首脑人物高克林、张达志、白成铭、苏谦益等全部遇险, 塞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曾锦云等5位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师、团级干部有3人牺牲, 两人负伤后去世, 另有班、排、连级干部多人阵亡或负伤。黄树坪战斗是八年抗战时期我晋绥地区牺牲极为惨重的一次战斗。

1945年深秋于左云县。左起:王宝烈士之女、小八路王生梅,王宝烈士生前的亲密战友、原红25军老战士杨福财,本文作者、小八路王生明。
我当时只是政治部宣传队里的一个小兵, 本来不具有撰写这篇回忆文章的资格和能力。只因至今无人动笔追记那次非同寻常的战斗, 一种对历史的责任感驱使我拿起笔来, 补记这悲壮的一页, 以慰先烈。
欢声笑语的陈家营村
1944年春, 偏关县城东40华里的陈家营村, 不声不响地变成塞北军分区司、政、后机关的“娘家”村。在村前宽阔的关河滩上开辟出操场, 竖立起篮球架、双杠、单杠和木马。一大早, 悠扬的军号声似乎在向人们示意: 敌人远在白云蓝天之外, 这是一个和平安祥的日子。操场上照旧是劈刺、投弹、打靶训练, 不久前本部宣传队排练的《血泪仇》、《打得好》、《刘五翻身记》等歌剧、话剧、哑剧在这里演出后, 更加给人一种生机勃发的印象。
9月间, 应塞北工委书记高克林、塞北军分区司令姚喆等军政首长的邀请, 贺龙同志苦心组建的“七月剧社”首次来塞北前线进行慰问演出。“七月剧社”来到不久, 姚喆同志即回后方汇报工作。
“七月剧社”的新式舞台布景和众多大型现代与古装剧目, 使大青山归来的步、骑兵健儿大饱眼福。根据地的红火热闹, 我骑兵一、二、三团, 骑兵大队(前身即王老虎(王零余)率领的120师独立六支队骑兵营)、步兵二营在外线作战的胜利局面, 使侵华日军恼羞成怒, 慌恐万分, 暗中策划着一次“围剿”。10月中旬, 日寇兵分五路, 向陈家营村合围而来: 驻绥远(今内蒙)清水河与暖泉的日军, 分两路从正北和西北方向围来; 驻井坪(今平鲁县城)之敌, 从正东方向围来; 驻朔县利民堡和驻神池之敌, 从东南方向围来; 驻五寨、三岔之敌迂回到河曲县境之后, 扭头从西南方向包抄而来。总兵力约有3000余人, 妄图一举拔掉我塞北抗日根据地。
我根据地军民的反“扫荡”策略是: 既不把外线作战的主力军调回来与敌人正面对抗, 也不远离“娘家”。而是依靠根据地的优势配合外线作战, 化整为零与敌人就地周旋。我司、政、后机关有意向敌显示: 你不来我不走、你不进村我就不出村的顽强姿态。
10月19日下午, 东南方向之来敌, 已与我骑兵一团的警戒部队交火。“七月剧社”仍旧从容不迫地打开古装戏箱, 为司、政、后机关和警卫连演出最后一场古装戏《千古恨》。这是一幕专门给日寇表演的“《空城计》”。
杀开血路冲出包围
20日清晨, 陈家营村依旧是那么平静。“七月剧社”的骡驮子天不亮就启程, 顺着关河大路急匆匆地向偏关县城方向走去, 那是一条通往晋绥边区首府——兴县蔡家崖的大路。我们塞北军分区政治部宣传队, 除十几名女同志和小兵外, 大都是整顿“三风”结束后尚未分配工作的军政干部, 有丰富的战斗经验, 因而与部队一样整装待命。与平时不同的是, 今天刚刚吃罢早饭, 曾锦云主任就站在宣传队驻地的窑头上, 催促宣传队赶快出发, 上北山!
我们20多个同志背着各自的背包, 顺着一条羊肠小道向北山爬去。上山后, 放下背包原地休息。敌人在哪个方向? 距陈家营多远? 一概不知。青年人照旧是说说笑笑。
突然间, “轰”的一声巨响, 一颗迫击炮弹落在我们正前方的山脚下爆炸。紧接着, 又一颗炮弹越过我们的头顶在山后爆炸, 顿时腾起一堆白烟。
敌人在什么地方向我们打炮? 还是无法判断。惊骇之间看到, 张达志副政委骑着他的“四脚白”(黄色马)从我们身后赶来, 警卫连一路小跑, 机枪射手张二扛着日本制造的歪把子机枪紧紧跟在首长的战马身后。当张副政委的坐骑跑出距我们停留的地方约50米的山坡上时, 一颗炮弹落在他马前15米处爆炸, 黄土碎石四溅。“四脚白”本能地将一双前腿腾空拔起, 但它随即轻轻地把双脚放回原地。当它的主人示意继续前进时, 它不顾枪林弹雨的阻击, 立即驮着它的主人向不远处的一个制高点奔驰而去。
此时, 西北方向的轻机枪声, 好似狂风吼啸, 所有的大山都颤抖起来, 共鸣起来。敌人与我北山上的阻击部队已经交火, 抵抗不住这路敌军, 我司、政、后机关人员就难以脱险。
然而, 大家看得清楚:“四脚白”抢占了制高点, 张副政委率领警卫连占领了制高点, 歪把子机枪射手、平鲁县向阳堡村姓张的青年战士占领了制高点, 他们为司、政、后机关杀开一条血路, 反“扫荡”第一次突围得以成功。但是, 追敌仍在身后。
热血洒在黄树坪
10月20日, 我塞北军分区机关冲破敌人的重重包围, 走山路向偏关县城方向撤离, 日寇在陈家营村一无所获, 犹如司马懿走到西城之下在“空城”前未敢久留, 拔腿而去。
这天, 我司、政、后机关甩脱追兵, 几经辗转, 绕过西北清水河方向之来敌, 在21日凌晨5时许, 与塞北工委机关一起到达距偏关城西南30华里的黄树坪村。
进村不久, 我哨兵即发现南山老维梁上有可疑人马在运动。
我哨兵向对方高喊:“哪一部分的?”
对方答:“五寨游击队!”对方接着反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我哨兵答:“塞北军分区!”
张达志副政委和参谋长邓家泰听了哨兵的紧急报告, 走出窑洞瞭望片刻。终因天色不亮, 一切都影影绰绰, 看不清楚, 难以判断是敌人还是友军。大家综合分析认为: 十有八九是敌人。但这路敌人从何而来?共有多少?已经占领了周围多少村庄?情况一概不明, 若仓促撤离, 盲目性太大。加之部队行军打仗一天一夜, 人未吃饭, 马未上料, 人困马乏, 敌人攻来难以对付。
于是, 张副政委果断发出命令: 警卫连加强警戒, 全体指战员放松休息15分钟, 喂马饮马15分钟, 吃饭15分钟, 就地待命。
可是, 未等45分钟的整备工作全部结束, 南山之敌已向我开炮。炮弹击中我村后一个制高点(小庙), 两名战士当即阵亡。敌人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 以“扇形”阵势从正南和西南方向冲杀过来, 我机关人员在警卫连机步枪火力的掩护下边打边走, 撤出村外。
敌人怕我调兵回师反击, 驮着几十具尸体仓皇逃窜。
第二天, 我军返回黄村坪清理战场, 在村后数十丈深的“堰角角”沟底, 发现我死伤人马几十具。政治部主任曾锦云同志的遗体仰卧在黄土地上, 他的胸部中弹。现场残留的纸片、相片表明: 他牺牲前就地销毁了随身携带的重要文件, 他与其妻子吴兰英的结婚合影, 也一并销毁。敌人脱去他穿在身上的皮大衣。这位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中, 先后9次负伤的老红军, 在抗战胜利的前夜, 长眠于此。在曾锦云同志遗体的不远处, 组织科长谢理云同志的遗体也被发现。在他的遗体身边先后找到他打过的十几枚手枪弹壳和被他撕成碎片的机密文件。据隐蔽在附近水涮洞的当地群众描述, 他挂花落马后仍顽强地和敌人拚杀。一名日本兵见他负伤, 跟着他的血迹追来, 妄图捕捉他, 被他用手枪击毙, 因而敌人对他的遗体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报复。司令部二科科长姚典训同志的遗体上, 也有不少弹洞和刀伤。
司令部副官(四科长)张逢福, 负伤后突围出来, 在离黄树坪20华里的河曲县境内被当地群众抢救生还, 但不久因病、伤交加不幸去世。司令部一科长吴玉德腿部负伤, 久治不愈, 卒于兴县120师医院。
在黄树坪村后, 还先后找到田永华、裴占元、张树林、丁辛、田占元、郑保义、胡班子、邱福生、乔丕宽、贾德胜、白海宽、孟照同等12位同志的遗体。
孟照同当年20多岁, 河北省人, 会武术, 善翻筋斗, 不论情况多么紧急, 他的号角嘹亮有力, 从不走调“卡壳”, 深受姚喆司令员和张达志副政委的器重。在他倒地前, 曾与十几个日本兵白刃相搏。
这年12月下旬, 部队返回陈家营村。到后方汇报工作归来的姚喆司令员与高克林、张达志、苏谦益等军政首长和塞北党政军民一起为曾锦云、谢礼荣、姚典训等黄树坪战斗中牺牲的烈士召开了追悼大会。同时在黄树坪村后一块名叫“南兔峁”的土地上立起两块石碑。
在一块石碑上刻着:
曾锦云, 江西永新县人。
姚典训, 江西安福县人。
谢礼荣, 江西吉安县人。
1944年12月25日立
距这块石碑5米远的地方, 立着另一块石碑, 碑上镌刻着以下12位烈士的名字:
田永华、裴占元
张树林、丁 辛
田占元、郑保义
胡班子、邱福生
乔丕宽、孟照同
贾德胜、白海宽
1944年12月25日立
(本文初草于1990年12月下旬偏关县招待所, 发表于1991年《山西政协报》)
本文作者:王生明 笔名端阳生。1933年生,山西平鲁县人。原晋绥五分区敌工科长、军分区直属武工队政治委员王宝(保)烈士之子。
本站编辑:林子
主办: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晋ICP备15001143号-1
Copyright Shanxi Jinsui Culture Education &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9号院国投财富广场4号楼313/314 邮编:100073 电话:010-63395639/63395661 邮箱:sxjs9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