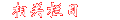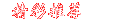
- 腊八节的思念(01月24日)
- 新年新风新气象(01月12日)
- 晋绥抗日老前辈牛文夫人晓民为烈士陵园捐树(01月05日)
- 新年贺词(12月29日)
- 贺晓明大姐向一二〇师学校赠送3D《中国地图》(12月28日)
- 岁末迎来晋南的客人(12月26日)
- 120师老战士后代来访(12月15日)
- 共商大计——保护开发利用好红色资源(12月12日)
- 沉痛悼念晋绥抗日老前辈支桂兰阿姨(12月12日)
- 百岁导演严寄洲与120师学校小剧社(11月27日)
让我们铭记在心的父辈友谊
发布日期:2016-10-15 04:28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作者:鲍去病
鲍去病 执笔
1924年秋初,林枫伯伯和我父亲鲍永瑞同时进入南开中学学习。从1924年到1926年底,大约两年半的时间,他俩同住一室,住在一起的还有张文佑叔叔。3人之中,林伯伯比我父亲长一岁,张叔叔居后。林伯伯在政治见识和活动能力方面见长,我父亲对人对事热情都很高,张叔叔耿直、持重。从考试成绩看,3人都是上乘,或都能上乘。张叔叔逻辑思维好,不大费力数理化就能考个好分数。林伯伯和我父亲的形象思维好,两人都喜欢文史;数学要考个好成绩,下的力气要比张叔叔大。他们深知学习机会来得不易,因此勤奋好学,能吃苦。父亲的经费不宽裕,为了买书攒点钱经常不吃早点。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林枫与南开同学的合影。右起:林枫、王少庸、张柏远。
同居一室的还有王少庸叔叔、张柏园伯伯。这几个人都堪称优秀,在同班同学中有一定的声望。班上其他肯上进而又表现不俗的还有杜毓云、江凌、李耕田等叔叔。这些人情投意合,相互敬慕,自然而然地聚在一起,无形中成了一个10人左右的群体。他们广泛阅读进步书刊,如《响导》、《新青年》及李大钊、鲁迅、郭沫若等人的作品,参加一系列政治活动,卷进了革命洪流。他们从学习和实践中懂得了革命的道理,其中,林伯伯、我父亲等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他们立志掮起黑暗的闸门,让劳苦大众奔向光明。
这一群年轻人在共同的学习和革命活动中建立了友谊,他们是同学,是同志,相互间有着一种特殊而又有别于兄弟之情的亲情;这种亲情贯穿了他们的终生。后来这些人的大多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有的成为职业革命家,如林伯伯为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奋斗终生;王少庸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作为八路军、解放军的干部,征战南北几十年;杜毓云成了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曾常驻印度;张柏园成了教育家;张文佑是李四光的大弟子,成为中外著名的地质科学家;李耕田则是医学专家。
1926年9月,北伐革命军打到武汉,举国震动,也打破了南开中学的平静,教师中的中共党员,秘密发动学生参加北伐国民革命军。我父亲从林伯伯那儿拿到去武汉参加北伐革命军的介绍信,计划在天津乘船南下去武汉。由于时局不稳,他们一个多月也未等到船,恰逢此时,父亲咳血住院,发现是肺结核,最终未能成行。此时父亲远离家乡,孑身一人,病魔缠身,又经济拮据,当时多亏了林伯伯这一群朋友多方照料。
由于结核病缠身,父亲不得不于1927年初离开天津回江苏沛县老家。此后,林伯伯等仍牵挂着我父亲,除书信往来,还寄些革命书刊。朋友们的鼓励和帮助,温暖了病人,这始终是父亲战胜疾病的力量。
1929年春,林伯伯到北平,写信建议我父亲来北平治病。这年5月,父亲抵北平,住进香山碧云寺疗养院,直至1931年冬。这期间林伯伯在北平大学工学院学习,张文佑、王少庸、杜毓云、江凌等叔叔们也在北平。他们虽在不同学校,却经常相约在一起,到碧云寺疗养院看望父亲。当时从城里到香山没有像样的公共交通,要骑自行车或骑毛驴上山,来回要大半天甚至一整天,去一趟是很不容易的;但经过艰苦跋涉后的会面,却成了林伯伯他们星期天的聚会方式。他们在碧云寺拍了不少照片,其中有一张写着“云间杏下”的照片人最多,我父亲、林伯伯等都在内,约有10来人。这当中也有不是南开中学的,他们是父亲这几个朋友的同学或友人。在我父亲原来不认识的这些人当中,有张文佑的女友刘蕴真刘姨。张与刘是唐山老家做主订婚的,起初张叔叔不想接受,但南开中学的这群朋友都劝他见见再说。可能是刘姨的父母刻意成全这门婚事的缘故,也把刘姨送到北平女子师范大学读书。张叔叔与刘姨在北平成为朋友,每次去香山,两人都一同前往。30年代初,两人就建立了家庭。他们的住处成了林伯伯在北平从事革命工作的秘密落脚点和避风港。

1930年5月鲍永瑞到北京碧云寺养病,与南开中学同学及友人合影。林枫(后左1)、鲍永瑞(后左3)、张文佑(前左1)、刘蕴真(前左2)。
对病中的父亲,林伯伯这群友人,除精神上鼓励、慰藉外,经济上也尽可能资助。由于疾病一时治不好,加上时局动乱,父亲于1931年冬离开疗养院回沛县。这年的秋天,由于不能跟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实现自己的抱负,而又即将别离,父亲在疗养院写过一首很动感情的诗:
秋到人间百感并,
最难排遣是离情。
天津慷慨悲歌壮,
燕市萧条孤月明。
我自终宵悲永夜,
谁同四海念苍生。
韶华如许病中逝,
一望行云一失声。
父亲由北平回沛县后,为了安心养病,没有住在鲍楼村的家中,而是在距家5里地的郝寨的一座小学旁边,盖了一栋茅草屋居住。当时父亲虽然重病在身,但意志并没有消沉,终日躺在床上读书看报。他订了多种报刊,如《大公报》、《申报》、《新民报》等。他读书的范围很广,包括古籍中的五经四书、经史、诸子百家等。父亲在读书过程中表现出坚韧的毅力。苍天不负苦心人,他的学识和人品,赢得当地村民的信任。乡绅们尊重他。教书的老师遇到了问题找他。郝寨的进步青年郝中士、郝中牟(李文)、郝心昌(王林岗)等更是经常到父亲的住处探讨时政。
郝寨人民从我父亲那儿间接地得知红军胜利的消息,了解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与腐朽,以及白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不屈不挠的斗争。父亲也在郝寨人面前常常直陈他对日本侵略者侵占东北三省的愤恨,对国民党卖国投降政策的不满等。这无形中启发了郝寨和邻村青年的革命思想和进步要求,对后来一些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33年和1935年,因北平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曾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的林伯伯,两次到沛县郝寨父亲养病的地方隐蔽。1933年住了一个多月,1935年住了两个多月。
沛县地处苏、鲁、豫、皖交界地带,居徐州市北70多公里处,在微山湖西岸。微山湖芦荡百里,云烟茫茫,乃卧虎藏龙之地。当时国民党在此也十分嚣张,斗争形势十分残酷,稍有闪失,革命就会遭遇不测。
当时,林伯伯以教员身份来到沛县,对外讲是来探视病友的。来后,林伯伯参与了当地“反帝大同盟”的抗日救国活动。2001年9月前后,王林岗(即郝心昌,2007年92岁,住在贵阳)、李文(即郝中牟,2006年病逝)曾口述了林伯伯当时在沛县的活动状况,由鲍庆林写成《沛县“反帝大同盟”发展始末》一文,现摘要如下:
“1931年郝中士(1938年任中共沛县县委书记)、鲍延年等人在北平参加了‘反帝大同盟’,1932年根据上级指示,回沛县家乡活动,带来了‘反帝大同盟’的组织关系,并秘密发展组织,很快就发展了从无锡教育学院学习归来的李剑波(1940年任中共沛县县委书记)、在沛县师范学校学习的郝心昌、在东海师范学校学习的郝中牟等。”
“1933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捕杀沛县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一次,国民党派兵包围了望湖村小学,抓走进步教师、职工、学生30多人,最小的年仅14岁。当时沛县的‘反帝大同盟’组织有30多名成员,直属北平总部下某分支盟的领导,与沛县党组织没有横向联系,故未遭到破坏。”
“林枫第一次来沛县是1933年冬天,住在鲍永瑞家。当时,‘反帝大同盟’的成员,通过鲍永瑞的关系得以与林枫会面。这次在鲍家与林见面的有郝中士、郝心昌、郝中牟等人。林通过鲍对沛县党组织惨遭破坏的情况有所了解,心情沉重,但对革命的最终胜利仍然充满信心。林讲了革命斗争的艰巨性和曲折性,但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有着无比光明的前途,是任何敌人都无法战胜的。‘反帝大同盟’虽未暴露,但不能放松警惕,更不能放弃斗争。疾风识劲草,一个革命者,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立场坚定,坚持斗争。像季米特洛夫那样,即使落到敌人手里,也要把敌人的法庭当作革命的讲坛。林的一席话,使我们增强了革命的坚定性,树立了革命必胜的信心。”
“林枫第二次来沛县是1935年6月。隐蔽在鲍永瑞住地,一刻也未忘记一个革命者的使命。在鲍永瑞病榻前,林枫与‘反帝大同盟’成员郝中士、鲍延年、郝心昌、郝中牟、李剑波等开过一次会。林在会上给大家谈了很多问题,记得主要是强调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特点和党的斗争路线的变化。他说,由于日寇加紧对我国的侵略,不仅东北三省沦入敌手,我们整个中华民族也面临亡国的危险。而国民党的卖国妥协政策,更加剧了这种危险。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党的斗争策略、方针也要随之变化。当前不再提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只提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只提‘抗日’,以‘抗日’为口号,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民众,发展革命力量。林还在笔记本上手书‘反帝大同盟’斗争纲领,写满了一页纸,撕下来,交给我们,大意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政策’等。”
“会后林枫还分别找我们几个人个别谈话,他循循善诱,引导大家应当怎样深入认识当前形势和革命任务;当斗争目标明确后,作为一个革命者应当怎样工作;发展组织,为党增加新鲜血液,是时时不能忘记的,但在步骤上要波浪式一步一步地进行;开展活动,要根据实际情况,大胆创新等等。我们都觉得他的话深刻生动,很有说服力,于是形成了一个共识:今后宣传党的纲领,要强调‘抗日’,以‘抗日救亡’为口号来团结群众。我们拟定创办‘齿轮社’,来团结知识青年,郝中士草拟了一个章程,林枫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在这以后,沛县反帝大同盟的组织工作有了起色,发展了一批成员,如黄天明(1940年任中共沛滕地区县委书记)、罗伯行(1948年任中共沛县县委书记)等,并成立了‘反帝大同盟’沛县临时工委。后来大部分反帝大同盟成员转为中共党员,成为我党开辟湖西区(即微山湖周边地区)根据地的骨干力量。”
“林在沛县的时间虽然不长,却推动了沛县的革命工作,直接间接地促使许多同志走上革命道路。他给我们讲的革命的坚定信念问题,革命的曲折性复杂性问题,革命的目标、路线、方针问题,学习马列和加强党的观念问题,发展组织问题等,至今言犹在耳。”
林伯伯在沛县虽然很隐蔽,但也引起当地政府的注意。一天保长郝中福借着收“壮丁费”的机会,闯入父亲的住房,窥探虚实。当时林伯伯正好在场,遂与保长理论了几句:“这是个病人,你还到这里收‘壮丁费’,简直是胡闹。”这下子,保长可找到了借口,态度嚣张,出言不逊。林伯伯实在看不顺眼,连推带轰,把保长赶出了家门。这还了得,惹得保长哇哇乱叫:“鲍永瑞你家有‘黑人’,我马上叫乡丁来抓!”
郝中士等人得知后,觉得事态严重,担心林伯伯的安危,于是请出郝氏家族有威望的族长做工作。族长把保长叫来,训斥说:“鲍 先生是咱们这一带德高望重、学识渊博之士,是咱郝寨请来的客人。人家是个躺在病床上的病人,你找他收的是哪门子‘壮丁费’?人家的同学,是在北京洋学堂里教书的,有大学问的先生,老家东北三省被日本占了,回不了家,来咱们这里看望朋友,暂住几时,这是看得起咱们。大家都是年轻人,在火头上吵几句也算不了什么;你说人家是‘黑人’,是共产党,哪有这个道理?你小子如果还想在郝寨混的话,今后就给我老实点!”保长被族长训斥一顿,心中有几分胆怯。郝中士又以本家兄弟的关系找到郝中福,以和稀泥的方式,对他抚慰了一番,于是这场风波便平息过去。
林伯伯两次来我们家隐蔽,全家对他关怀备至。我伯父是个饱读诗书的人。他认为林伯伯不为名利,是位忧国忧民的侠义之士。林伯伯的日常生活均由他操办。我母亲还给林伯伯做了多件新衣服。林伯伯来沛县期间,我的叔伯姐姐鲍延昭也在郝寨念书。林伯伯叫她小二头,两人相处得很愉快。天黑后,姐姐常陪林伯伯拿着手电筒,到村边树林去抓蝉的幼虫,第二天用油煎炸。林伯伯吃得津津有味。小二头放学回来,林伯伯经常给她讲一些有趣的历史故事,其中蕴含着不少革命道理。林伯伯还常带她在村边树林中嬉戏。林伯伯和反帝大同盟的成员见面时,就让她去放哨,有时还让她传递信件。直到她长大成人了才明白:“伯伯、叔叔在黑暗恐怖的年月,与敌人作斗争的过程中,把我当成了小交通员。”
1935年,我的叔伯哥哥鲍延矩也见过林伯伯,当时他仅7岁。受父辈革命思想的熏陶,1948年19岁时,他拿着沛县中共组织的介绍信奔赴解放区,在保定入华北大学学习。

1936年鲍延昭(小二头)抱着作者鲍去病,摄于江苏沛县郝寨鲍楼村。
林伯伯离沛前,由我伯伯经手,卖了家里200斗粮食,用卖粮食的钱送他上路。1935年林伯伯在我诞生前一个月左右离开沛县。当时日本正加紧侵略中国华北,在这种抗日斗争形势下,他对我父亲说:“这个孩子将会带来风雨。”父亲就借用产生在沛县大地的《大风歌》为林伯伯送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1936年林伯伯把郭明秋郭姨的一张比一寸稍大的照片寄到沛县,并在照片后面写了“何许人”三个字,让父亲猜猜这是谁?从此,父亲知道林伯伯身边有一个能关照他的伴侣,遂放心了许多。除了这一张照片外,还有一张郭姨在天津划船的照片,梳着短发。

1936年,郭明秋(右)在天津宁园本
在我父亲保存的照片中,还有几张弥足珍贵。一张是上个世纪30年代初照的,刘姨坐在前排中间,林伯伯等人站立在后排。还有一张是林伯伯、王少庸、张柏园3人,穿着黑色大褂,看样子好象是30年代后期照的。在这些老照片中,还有抗日战争时期王少庸及蔡姨的,张柏园、杜毓云、江凌、李耕田等人的。在敌占区的沛县保存这些照片,有相当大的风险,一二十年来都藏于沛县鲍楼村我们家后院的西墙中。在相册后面一页,我父亲写过这样几句话:“此册订于1937年春末。当年12月日寇炮火迫近,藏于壁中。1939年夏大雨壁湿,启视晾晒。1943年修理房屋,又取出。后一直沉埋到日寇投降,于1945年9月重见阳光。1946年秋至1948年淮海战役前,又‘韬光晦色’二载有余。”
这些照片的下方大都有父亲的题词。郭姨照片的下方写着“何许人”。
王少庸、蔡姨夫妇两张照片旁边写着:
群芳都是岁华侣
你伴桃花她伴梅
有一张是南开中学六位同学在天津“八台山”划船时照的,题词是:
城南烟水应如旧
天涯何处再同舟
另一张是张文佑叔叔为我父亲拍的、躺在病床上的照片,题词是:
莫道闲情抛弃久
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
从这些题词中,可以感受到特殊而又有别于兄弟之情的那种亲情。说到照片,还得提起藏书。父亲的藏书中,有在南开中学阅读的,有30年代林伯伯他们从北平寄到沛县的,也有抗日战争期间郝中士、李文、孟广彬(1945年任中共沛县县委书记)、李剑波等人秘密送来的有关抗日斗争的书刊。这当中有《新青年》、《世界文库》、河上肇著1929年再版的《经济学大纲》、《海上述林》(两卷)、《鲁迅书简》等。《海上述林》是当时在北平的李耕田预订的。1936年底、1937年初分两次由上海寄到沛县。《鲁迅书简》也是1937年父亲的这些朋友们跑遍大半个京城买到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这些书装在两个1米 多高直径半米左右的砂缸里,埋在后院地下,每年夏天雨季后挖出晾晒。每当晾晒时,我们小孩子都要在大门口放哨。
1947年父亲去丰县晓明中学教书。1948年沛县解放,沛县县委书记罗伯行邀父亲到沛县中学参加接管工作,担任了校政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同时教课。沛县解放,父亲与林伯伯很快就取得联系。北平解放后,当年南开中学的几个同学江凌、杜毓云等也到了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江凌叔叔在教育部任职,遂调父亲来中央教育部工作。我跟随父亲于1950年5月4日 抵京。来京前,父亲同林伯伯说过调动工作的事。林伯伯不主张至少未提出调京工作。林伯伯说,在沛县做个教书匠也很有意义。我猜想,林伯伯或许觉得,父亲在沛县是知名人士,当地知道他的为人,曾为革命出过力,有一定影响,到北京这样的环境,不一定能适应。不过,教书匠的“匠”字却给我很深的印象。石匠、木匠、铁匠,唯有达到“匠”的境界,才能对社会更有用,也才能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
建国后,林伯伯与我父亲的第一次见面,大约在1950年至1954年期间,林伯伯利用从东北来京开会之机安排的。这是他们阔别十五六年之后的见面。
1954年林伯伯全家迁到北京,打这以后至1965年,他们虽忙于工作,但郭姨仍安排原南开中学的一些朋友在他们家聚会,最常去的是父亲和张文佑,杜毓云等有时也去。这种时候,郭姨总忙里忙外安排大家吃饭。他们偶尔也在公园聚会,这种情况,大家把子女也带去。与日夜操劳工作相比,聚会和见面是林伯伯他们最轻松的时候,也是说不出有多么愉快的时候。平常,父亲也单独去林伯伯家。有一个时期,我家与张叔叔家相距不远,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
1950年前后的一两年,父亲在京的薪酬是供给制,每月400斤小米,没有多少钱置办衣服。林伯伯、郭姨利用来京开会的机会,带给父亲一些衣物,其中有一件御寒的皮大衣,还有一部20卷的《鲁迅全集》和一方砚台。父亲去和平门外琉璃厂买旧书的时候,偶遇魏碑拓片集,也想着买下来送给林伯伯。林伯伯喜欢这种碑文字体。在南开中学的时候,父亲给林伯伯刻过一方印章。50年代一次见面时,林伯伯曾说,战争年代,许多东西都丢了,这方印他们一直带在身边。
1954年以后的一段时间,林伯伯在国务院管教育工作,我父亲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中学语文教材。他们见面时不免谈起教育和孩子们的学习问题。林伯伯说:应当从小就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劳动习惯、锻炼习惯、卫生习惯。这几个习惯的说法给我的印象很深。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批专家编了一部《古代散文选》,我父亲是编辑之一,曾送给林伯伯一部,后来,郭姨又买了多部送给他们的友人。林伯伯看到父亲参与编写的书籍、教材、刊物很高兴,曾对郭姨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我的这位老朋友,在病床上躺了十七八年,现在在语言文学专家圈子里也能立得住。”1949年前后,郭姨还为我们小孩子订阅了东北解放区的书刊寄到沛县。郭姨每次见到我和妹妹延敬,常问起我们学习情况。先人曾说:“脍炙愉我口,知识真理悦我心”。父辈对书籍、知识的珍视和向往深深地影响了后辈。
1966年林伯伯横遭迫害,从1967年起我们就得不到他们全家的一点信息。我们也去打听过。不久我父亲去河南干校劳动。大约1970年,我正在西部大三线工地做现场设计,从北京转来耿耿一封信,知道他们姐妹一点情况。此后不久,利用返京的机会,我按照她信中写的地址去找过她,结果并未见到。随后我即离京去西部大三线。
郭姨住在三里河附近的时候,我曾多次探望。90年代初,我对延矩哥说起去看望郭姨的事,提出要延矩给郭姨刻个图章。不几天图章就刻好了,共两枚,是很普通的青田石,一大一小,我送给郭姨。她对雕刻的篆字之美颇为赞赏。我也觉得这是延矩刻的数百枚图章中耐人寻味的那一类。
“文化大革命”中期,父亲就已退休回沛县老家定居。他每年都回京几日,住在我家里。1972年之后,林伯伯住在阜外医院。我都陪父亲去看望。只见两位老人温文尔雅对面而坐,相视微笑不语。父亲每年来京就每年去阜外医院六病房探视,直至他自顾不暇无法来京。1977年5月30日 ,父亲在沛县溘然长逝。同年9月29日 ,林伯伯也永远离开了我们。啊,让我们铭记在心的父辈,让我们铭记在心的父辈友谊!
作者:本文由鲍去病、鲍延矩、鲍延敬共同回忆,鲍去病执笔。鲍去病、鲍延敬为鲍永瑞的儿女。鲍延矩为鲍永瑞的侄子。鲍去病1935年出生于徐州沛县;1962年起在第五机械工业部第五设计院工作;80 - 90年代先后在国家机械委机械电子工业部经济技术政策研究所工作,副所长,研究员;兵器工业总公司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本站编辑 林子
主办: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晋ICP备15001143号-1
Copyright Shanxi Jinsui Culture Education &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9号院国投财富广场4号楼313/314 邮编:100073 电话:010-63395639/63395661 邮箱:sxjs9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