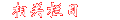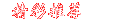
- 腊八节的思念(01月24日)
- 新年新风新气象(01月12日)
- 晋绥抗日老前辈牛文夫人晓民为烈士陵园捐树(01月05日)
- 新年贺词(12月29日)
- 贺晓明大姐向一二〇师学校赠送3D《中国地图》(12月28日)
- 岁末迎来晋南的客人(12月26日)
- 120师老战士后代来访(12月15日)
- 共商大计——保护开发利用好红色资源(12月12日)
- 沉痛悼念晋绥抗日老前辈支桂兰阿姨(12月12日)
- 百岁导演严寄洲与120师学校小剧社(11月27日)
老兵来信6:我是这支功勋部队的第一批兵
发布日期:2017-07-17 11:39 来源:军事--人民网 作者:温宪

从北京第50中学参军战友合影,前排中为本文作者温宪。

1996年2月27日,时任人民日报驻南非首任记者的作者在南非罗本岛监狱曾囚禁曼德拉的牢房内进行采访,也是第一位赴罗本岛监狱采访的中国记者。
1969年12月18日,我以“甲级身体”的评定从北京第五十中学穿上了那身“小帆布”军装,开始了军旅生涯。在前往陕西华县的“闷罐车”中,两排人的身体随着车身整齐地左右摇晃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
四年多当兵的经历,是我生命中永远难以忘怀的人生第一篇章。
我和其他战友从北京来到秦岭脚下,成为刚刚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回收部队第一批兵。
作为我国唯一一支卫星和载人飞船回收部队,这支部队使命庄严,任务神秘,功勋卓著。2005年,我的老部队被中央军委授予“功勋着陆场站”荣誉称号。
神圣的使命感、高度的责任感和光荣的自豪感一直是这支部队的血脉。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记得当时在陕西华县西马村一间只能爬着才能进去的农舍阁楼上听到这个消息的,我感到非常自豪,因为我是这支光荣部队的一员。数十年来,这种光荣与自豪伴随着我和我的战友们,也一直对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有着一份难以割舍的牵挂。
作为这支部队的第一批兵,我经历了许多,最大的收获莫过于咬牙吃了人生中最大量的苦,也因此在此后的人生道路上不再感觉有我不能吃的苦。“能吃苦”成为我极大的一笔人生财富。
我曾在烈日队列训练中晕倒;我曾因睡梦中常常吹起的紧急集合号高度紧张;我曾很不情愿地半夜起身站岗放哨;那时的伙食是一周只有周日上午一顿带肉;那时我们将旧信封拆开反折后粘好再用;当兵第一年,我每月只有6块钱的津贴,而一年后我向家中寄回了60元。
大雨滂沱之中,我们曾高喊着“打倒帝修反”的口号冲进长满芦苇的荒溏,奋力拔除芦苇的双手割出一道道血印,踩上尖锐芦根的双脚被扎出一个个血洞。寒冬之中,我们急行军数十里至秦岭脚下开荒种土豆,出了一身又一身的“白毛汗”,只得脱下全部湿透的厚棉衣晒在寒阳下。为了盖营房,我们进山搬石头,用卡车拉木头,我右手中指不幸被巨木挤压至卡车厢板后变形。我们曾急行数十里进入秦岭,将打捆的树枝背回。回程的山路显得那么漫长,肩头的树枝愈显沉重,我们一个个一步一歪地走出山外。
我曾随大部队赴陕南山区拉练。作为炊事班长的我身背一口大黑锅,锅的黑灰涂满全身,使我成为整个部队知名的“黑人”。就在那次拉练中,我才知道山中的百姓一年只吃一次肉,一天要翻过几座山,干重活的当地汉子一天只喝一碗稀粥。当我拉着风箱蒸馍头之时,一个女孩一直呆在大锅旁,我永远忘不了她那饥饿的渴求眼神。我也忘不了那天起早做饭时,在黎明前的夜色中担水竟迷了方向,“鬼打墙”似地转了一圈又一圈。
我曾随大部队赴四川演练回收卫星。忘不了一毛钱买的鸡蛋汤竟是那样丰盛,也忘不了第一次见到松花蛋时不敢下口,以为那是坏掉的鸡蛋。一位挑着重担轻盈奔走的姑娘让人见识了当地人的吃苦耐劳。“单砖立墙墙不倒,草绳拴猪猪不跑”的笑谈也令人印象深刻。
那是一个文化生活极度匮乏的年代。我的部队曾长途行军,为的是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事前还被提醒多带两块手帕,以备泪如雨下。我目睹了华县县城因放映朝鲜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造成了怎样的拥挤,一个孩子不幸被人群踩踏在地下。当我在人群中抢抱起孩子飞奔送至县医院,但第二天仍得知孩子不幸离世。
我忘不了中队指导员李新纪。他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为优秀的基层干部。在一个极左的年代,他一直与人为善,有着极强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成为他留给战友们终生难忘、至今仍感到温暖的遗产。今年早些时候,我的一些战友从北京出发,专程赴指导员的河南老家,代表所有战友在他的墓前祭奠缅怀。
我忘不了中队长王喜彬。他是我所见过最具有干练气质的军人。人称“大胡子”的他极具威严,却又令人心悦诚服。我至今仍能回味他用略带沙哑的嗓音称我“二班副”时的亲切。
这是一段用摸爬滚打锤炼出纯洁友谊的人生。几十年来,新闻工作者的职业使我在世界四大洲范围内阅人无数。但没有任何一段人生中的任何一个群体在我心目中占有如同“战友”一样的位置。较之职场,战友之间基本没有勾心斗角的利益关系,没有循规蹈矩的繁文缛节,没有虚情假意阿谀奉承。我们只是大写的“战友”。
近半个世纪以来,每当需要介绍我自己时,我告诉对方:“我是当兵出身”。“你像是一个当过兵的。”每当听到这样的评价,心中顿涌惬意。每当见到一位当过兵的人,彼此间的距离便由一种注定的亲切感拉近。
这是一段浸入骨髓的人生。我是一支功勋部队的第一批兵,我因此感到自豪。(温宪,人民日报社原北美中心分社首席记者)
本站编辑 林子
主办: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晋ICP备15001143号-1
Copyright Shanxi Jinsui Culture Education &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9号院国投财富广场4号楼313/314 邮编:100073 电话:010-63395639/63395661 邮箱:sxjs9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