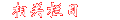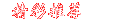
- 春节前又见老阿姨(02月06日)
- 基金会携手中青网传承晋绥红色文化(02月06日)
- 晋绥儿女的情怀(02月05日)
- 腊八节的思念(01月24日)
- “大寒”——林炎志大哥在京的一天(01月21日)
- 新年新风新气象(01月12日)
- 晋绥抗日老前辈牛文夫人晓民为烈士陵园捐树(01月05日)
- 新年贺词(12月29日)
- 贺晓明大姐向一二〇师学校赠送3D《中国地图》(12月28日)
- 岁末迎来晋南的客人(12月26日)
红军征途中的饮食
发布日期:2017-09-05 11:17 来源:人民政协报 作者:杨建民

峥嵘岁月 (油画)1979年 林冈 庞涛 作

刘毅长征途中采的野菜 国家博物馆藏
本文中介绍的红军征途中的饮食,均来自于参与长征的红军干部战士的记述。仅仅通过这些记载,长征的艰辛困苦便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任何艰苦条件下,不屈服,不畏惧,即使在吃的问题上,也能显现出一种精神。它作为长征精神的一部分,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这是作者专门从多种文章中寻出长征饮食作为题目的初衷所在。
“走到哪里吃到哪里”
长征的出发较为仓促,这是一次大规模的长时间行军作战,在饮食这个基本问题上,是无法考虑更多和长久的。1949年后担任过驻外大使、中联部常务副部长李一氓的回忆是:“大军出发,是个没有后方的战略转移,前面既无粮仓,后面亦无后勤供给,只能够走到哪里吃到哪里。”
“走到哪里吃到哪里。”那么,也就是有什么吃什么。有时情况好,就可以吃得好,条件差,吃得自然差,饥一顿饱一顿。见不到人烟时,就没有或很少有吃的。时间长了,带在身上的一点粮食没了,只好向大自然讨要。在这后面,李一氓还有话:“至于吃谁,当时大家都很清楚,我们有一条阶级路线,主要吃地主的粮仓、牲畜等。”这种情形下,队伍管理也比较严格,每个伙食单位不能单独、自由行动,必须统一在一个名为“供给部”的领导下,指定到什么地方去领什么东西。李一氓记述:“如那个地方有地主的鱼塘,就可以分到鱼。我还记得在湖南的一个大村子里,我们分得很多塘鱼,这是第一次,真鲜美极了。”
部队走到云南宣威,居然分到了全国有名的“宣威火腿”。这东西,当时主要是有钱人享用的,一般人连怎么吃都不会。据李一氓回忆,他们连队的炊事员“根本不知道如何烹饪这种东西,而是切成大块,采取类似烧红烧肉的办法,结果一大锅油,火腿也毫无味道。”但也有吃过并知道如何制作的人。1949年后曾担任过解放军海军司令员的萧劲光(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他就不要公家烧的火腿,而是让分一份生火腿给他。他把这火腿蒸熟,搁在饭盒的菜格子里。这样,每天行军正午休息吃午饭时,他就打开来下饭。李一氓称其“聪明”,还羡慕地说:“这种味道当然比红烧火腿有意思多了。”
但是,这样的日子并不多。绝大多数时间,有一顿正常的米饭就很不错了。在一位名叫谢扶民的红军写的一篇日记《苗山一夜》里,写到长征到了大、小苗山时,老百姓都躲进了山里。经过一位老人出面说服,百姓才回到家。战士们以六块大洋100斤的价格,买到了部队需要的大米。可在分发的时候,一些单位却不愿意要这些大米,说买到的都是糯米,这种米,吃了不管用,行军“脚发软,走不动路。”经过了解,才知道这块地方只产糯米,没有其它粮食,大家只得收下。一些人开玩笑说:“好吧,就算过一个年节吧。”因为在大多数地区,只有在过年过节时,才舍得用糯米做些年糕、甜米饭之类的食品。这说明,当时部队行军,是走到哪吃到哪,有什么吃什么,没有多少可以挑选的。
这是正常时节,还有许多时候,部队走的是偏僻山地,或荒无人烟的草地,时间久了,吃食就出现问题。据1955年授予少校、长征时的小战士谭清林回忆,1935年秋,他所在的红四方面军越过大雪山,在草地边缘的康猫寺休息两三天后,没有找到什么粮食,只好采集了一些松菌、松果,烤熟了一些牛羊皮做干粮,随即向草地进发。他所在的三十军九十一师一个连队,进了草地几天后因为大风冰雹,找不到前面队伍留下的路标,只好返回出发地。等到再出发时,原来准备的干粮松果、松菌之类都吃光了,再找不到吃的。进入草地那天,只有他自己的最后一小把炒面,分给几个战友各人“一小撮”,就着雪水吃了。在草地中,头两天大多数人只能喝一些带有草味的黑色苦水,吃一点随手拔起的野草、野菜。找不到青草时就抓起枯草,嚼嚼草根,咽些口水。后来几乎沿途所有野生植物,都被大家尝遍了,之后发现一种满身长刺的矮树,上面叶子落光,结着豆子粒大小的红果,吃起来味道酸甜酸甜的,这算是最好的食物了。见到这样的树,大家都一口气跑过去,满口满口吃饱了,还要折下几枝,带给伤病的战友。可这样的尝试也带来灾难。第二次进草地第六天,有人在地上扒出一种青萝卜一般粗大的水生植物,刚试着吃时,味道甜还爽脆。得知这个消息,大家都分头去找。谁知这东西吃下去不过半个小时,毒性发作,呕吐不止。有人好心舀碗凉水给呕吐人喝下去,不料呕吐更厉害。几位战士当场牺牲。这以后,大家采到野草野菜时,总是先放在嘴里小心嚼嚼,多试几次后才敢咽下肚去。
雪山顶上的山药蛋和草地里的“皮货”
1949年后曾担任过原兰州军区司令和福州军区司令的皮定均(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开始长征时,才不过16岁。在攀越大巴山前,班长给了他一个“猪肠子那么大的干粮袋,一半装的炒熟的黄豆,一半装着剩下来的炒饭。”在皮定均看来,这点东西,还不够他一顿吃,可现在却要做几百里山路行军粮食。人小,不知利害,肚子一饿,他便偷偷抓炒黄豆往嘴里喂。一吃黄豆,口渴起来,乘班长不注意,抓一个雪团丢进口里,“用舌头压在一边,不但不觉得凉,而且精神焕发,越走越有劲了。”不长时间,皮定均携带的干粮被偷吃得差不多了。当副班长检查他的干粮袋时,距离他们的目的地还有“两个七十里”:“小伙,这怎么行呢,山还没有到顶,你的干粮就快吃光了。你不打算过去吗!”说完后,塞给他一个山药蛋。再三叮嘱:“你可要慢慢啃,不要一口吃光了。”
干粮不够,攀爬寒冷的高山是很危险的。后来,皮定均不敢轻易动这颗山药蛋,肚子饿时只是伸手摸摸。到山顶,已是夜深。大家肚子都饿了,皮定均拿出山药蛋,让给同志们。大家都是用门牙轻轻啃一下,又还到他手上。在山药蛋的支持下,大家度过了这漫漫长夜。下山后,副班长又掏出最后一个山药蛋,让全班战士啃。终于,这个大家都不肯吃的山药蛋,又到了最小的战士皮定均手里。他推给副班长,副班长对他说:“小伙,马上就要投入战斗了,你赶快吃了,鼓足劲消灭敌人!”多年后,皮定均以《两个山药蛋》为题,写下纪念文章。他在文章最后说:“这座大巴山,是我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遇到的第一座高山,也是我在斗争道路上所经历的第一道关口。……那里有我们的足迹,那里有我们全体战士同艰共苦的友情。这种友情,就象(像)大巴山一样,屹立在我心中。”
长征中吃皮带的事,1949年后曾担任过原成都军区副司令的李文清(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在《最后的脚印——记红二方面军过草地》文中有确切记述。作者所在的红二方面军五师十五团是从甘孜进入草原的。当时每人带了半个月左右的粮食(每人每天三四两计)。这点粮食,很快就消耗殆尽。一天,李文清到师部汇报工作。进了帐篷,闻到了一股香味。师长王尚荣(1955年被授予中将,曾担任过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拉住他:“先别忙汇报,这里搞了个牦牛脑袋……来!先喝它一碗。”“我接过来咕咕一气就喝了下去。多香呀!我好像这辈子第一次喝过那么好的汤。……而且,这锅汤是整个师部喝的。”此文中也记述了吃毒草的情形。因为他们是后卫部队,在草地上连可吃的野菜也几乎没有了。为了活命乱挖,结果就挖到有毒的草:“有的吃上毒草,轻的就会四肢抽风,神经失常,口吐白沫,重的就会丧命;当时又缺医药,大家围在一起束手无策,眼看着自己的战友倒下去,丧失了宝贵的生命,心里象(像)刀割一样难受。”
在这种濒临危亡的情形下,吃皮带这种极端行为,也就容易理解了。那是快走出草地前的一个星期,因为根本没有粮食,前进的速度也“慢得异常可怕,每天只能走八里十里。”有一天,一个通讯班的小鬼饿得实在不行了,就把皮带放在火上烧,然后用刀子把烧焦的部分刮掉,切一块嚼一嚼。虽然苦但是可以吃。“这个意外的发现马上就在全团推广了。于是,枪皮带,腰皮带,皮挂包,只要是皮,全吃光了。”
就连牛皮一类平时几乎不可吃的东西,长征中获得也不容易。据一位名赵连成的红军在《咱班的“王政委”》一文中记述,他们部队刚进入草原时,看到了先头部队丢下的一堆牛皮,他和另一位战士把牛皮拉回来,交给队长、指导员。领导将这些牛皮给每人分了两块。大家把小一点的牛皮用棕绳穿起来绑在脚上当鞋子,大块些的缝成一个带尖的帽子戴起来,有人还随手画个五角星在上面。走着走着彻底没粮了,这些“皮鞋”“皮帽”,陆续进了肚子。
打猎和吃青稞
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有时即使有较好的食物,无法以好的方式制作,吃起来也不是滋味。在李天焕(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曾担任过公安部副部长职)的长文《气壮山河———红西路军远征记》中,记述了他们在祁连山作战时,没有粮食,便让身体好、枪法准的同志到山上猎野牛、黄羊。其他人拔草、捡牛羊粪,准备用来烤火和烤肉。不久,打猎战士回来,抬着野牛、扛着黄羊。大家用刺刀割肉,每人拿一块,找块平整些的石头,或者挂在小树上把肉切成小片,再用枪探条串起来,在牛羊粪火上烧着吃。开始大家饿极了,肉烧得半生不熟便送到嘴里吃起来。吃过几块后,感觉不好了。野牛羊肉本身膻味很重,没有盐,用的又是粪火直接烧烤,那肉真是又膻、又苦、又臭、又腻……再饿也吃不多,勉强多吃就要呕吐。一个小战士机灵,他把肉放在脸盆里烧,不直接用粪火烤,结果味道少了苦和臭味。可惜,当晚落雪,这位睡在草地上的小战士竟然被冻死,连名字也没留下来。
这还是有猎物可射杀,没有的时候,为了人能活命,只好宰杀用来驮物资的牲口。吴先恩(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的《党岭山上》一文里曾记载,部队在过西康丹巴一带的党岭山前,宰了两匹牲口,“把肉分给伤员,皮和骨头给工作人员分了。”李文清的文章中,也有相同的记述:“情况已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了。为了救下这些革命的种子,现在,只有把最后一手拿出来了———把驮帐篷、物资的牦牛和首长骑的骡子杀了。杀一头全团要吃三四天,先煮汤和着野菜吃,再把煮过的肉分给每人一二两带着,不准吃,第二天再煮……”有牲口可宰杀,在长征中还算是较为幸运的。苏红的《红色少年连队通过草地》一文,记述了最早进草地时吃青稞的情形。此文介绍,当时吃的是“青稞囫囵饭”。这东西很难煮。炊事员为了第二天早晨大家吃好,居然一夜未眠煮青稞。吃饭时,一次三五粒嚼碎下咽,才会稍好消化。可人大多数时间大口吃着,结果就消化不了。在钱治安的《一次支委会》一文中,就记载了有关青稞的情况:“离德荣还有好几天路呢,全连就颗粒不剩了。这是我们连第一次经受饥饿的考验,饥饿第一次把我们带到生死存亡的边缘。据前面部队介绍,马骨头和马粪中没消化的青稞,都可以用来充饥。”牲口胃的消化能力强大,可也不能将青稞消化掉,可见其不便成为人类食品。
有关青稞在长征途中的故事不少。文人出身的李一氓,大约因为记忆深刻,故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还专门对青稞在当地生长和食用的情形作出记述:“稞麦就是大麦的一种,全名叫‘稞大麦’,因为生长期快,3~5月播种,7~9月收获,非常适合于青藏高原的地质和气候。……这种作物很经得起煮,用水煮了几小时后,仍然是一个个完整的麦粒。以为熟了可以吞食了,但还不能消化,排泄出来的还都是一粒粒的青稞。因为每个人分得的数量有限,有的甚至把排泄出来的青稞淘洗过后,再煮再吃。”粮食缺乏的情况,由此可想而知。
买食物和“借”食物
食品的来源,也五花八门。时任红四团六连连长的杨信香在《攻破腊子口》一文里记述,1935年9月中旬,红一方面军来到距离腊子口15里的地方。先头部队经过战斗,击溃敌人一个营,还缴获了大批面粉、白糖等。后来在攻击腊子口前,炊事员便用白天缴获的白面,给大家做了一顿好饭。吃饱后,战士们几番进击,打开了腊子口,使这支部队可以顺利北上,与陕北红军会师。这次的粮食,是从敌人手里获得的。
从多数记载里可以看出,虽然粮食总体缺乏,可部队的政策还是严格执行的。譬如对从百姓那里获得,大都需要购买。1955年被授予少校的康正德在《心连心》一文中记述,红四方面军行进到原西康省一个叫波巴的村寨时,为尊重少数民族,决定不进房子,在村外露营。当时百姓大约受到敌人宣传,都带着牛羊上了山。为了获得他们支援,战士们便分成若干工作队去山上寻找。藏胞们先有人回家,看到他们门上的锁、红布条、神符都原封未动,夹墙中的东西一件不少,而战士们却露宿村外受冻,吃着清水煮野菜,十分感动。他们回山,告知其他人,老乡们便赶着牛羊从山上草地回来。在一位老人的带领下,藏胞焚香点烛,硬把战士从村外请到家里。有的把在地下埋藏三年多的腊肉也挖出来给战士吃。还一下子慰劳了300多只牛羊来。当时红军不熟悉藏胞习惯,没有接受,这使藏胞很不高兴。战士看到藏胞没有盐吃,有钱也买不到,便将自己带的盐送给他们,可藏胞无论如何也不接受。后来通过翻译,战士们才知道没有收下藏胞的东西,是把他们当“外人”,因此藏胞很生气。于是,战士接受了他们给的粮食和肉,给藏胞一些盐,藏胞收下,之后便亲如一家。
在钱治安《一次支委会》一文中,还记有部队进入到德荣县城后,没有找到一粒粮食,战士本以为进了县城,可以得到一点补充,一些战士,看似病重,其实是饿的,有了粮食,吃饱了,病就好了。后来在几间破房子中,发现埋在地下的一大缸青稞。有了粮食,这本是大好事,可在藏区,部队有严格要求,不能随便动他们的东西。在饥饿和政策面前,连队开了一次支委会。在维持纪律和饥饿的实际情况下,经过争论,支委会通过了以白洋买粮食的决定。大家将地下400来斤青稞挖了出来,按照病号每人8小碗,一般同志5小碗,干部每人3小碗分发。在藏粮食的地方埋大洋时,领导让文书写了一张纸条,上面说,老板,实在对不起,我们挖了你的青稞。现将青稞折合五十块白洋留给你,请收下。落款是:中国工农红军三连全体。纸条是红色的,50块大洋用蓝布包了两层,红纸条端正贴在上面,放进装青稞的缸里,一个战士怕不够,又添了12块云南小银币。“这时候,支部委员都站在旁边看着,直到原封原样地埋好以后,他们才像放下一副沉重的担子,各自散去。”
肖永银(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是西路军战士。1937年西路军在甘肃高台、酒泉之间遭到极大损失后,他受令掩护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回中央。其间为有人能回到中央汇报,徐向前决定兵分几路,分别向陕北方向突围。肖永银与总部参谋陈明义两人一路,带着一个皮包和徐向前写给中央的信,以及几只做盘缠的金戒指,往中央方向进发。在路上,他们没有东西吃,也不敢轻易下山去买。在黑河边看到一户人家,他们便脱下军衣,化装成老百姓的样子去找饭。可遇见的那家汉子狮子大张口,听说他们要吃一顿饭,竟然要收5块钱。当时5块钱不少,一般一顿饭不过1角2角。这位汉子也许听出他们是外地人,要敲他们竹杠。可肚子里几天没食了,没有办法,就掏出一个金戒指当饭钱。那个汉子试了又试,终于收下,给他们做了一盆青稞面疙瘩。饿坏了,也不管烫不烫,呼噜呼噜吃起来。一连吃了七八碗,把肚子胀得发痛,可还想吃……再往前走到永昌城,天下大雪,老百姓家也不敢去,躲在野地会被冻死。想想,上一年部队经过时,住在城北半山腰的一座庙里。到了庙里,四处看去也没法躲,最后从后面钻进一尊几丈高的大菩萨的肚子里。睡了一觉醒来,出来找吃的,看到祭台上香烛还燃着,台上还摆着一些残存的供品。他们先捡起来吃了一通,再把剩下的装进口袋,扛着出了永昌城。这是向菩萨“借”食物。再往后走到一处名为“十二洞”的小村子,他们每每靠讨食维持。这天讨饭到了一大户人家,被狗咬了一口。村子里的人怕他们“找事”,便一家一户地凑了半布袋饭。凭着以血换来的“饭”,他们才度过了最艰难的一段岁月。
吃肉在当时的条件下很难得,可也偶尔能够碰到。据1955年授予大将军衔的徐海东回忆,他所在的部队,四处打听中央队伍。在甘肃与“马家军”打了几仗,进入到了陕北边沿白区红区交界的绍山地界。部队翻山越岭走了3天,也没有碰到一个村庄。背的粮食吃光了,“全军两天没吃上东西,许多同志饿得昏倒在路上。”这天下午,忽然发现了有500多只的一大群羊。上前一问,才知道是一个羊贩子赶到他处倒卖。经过和羊贩子“好商量一番,他才把羊卖给我们。”部队一下子就有了吃的。这次吃羊肉,没有盐,连锅也不够。这时,有脸盆的,就用脸盆煮肉;没有脸盆的,只有把肉切成薄片,放在石板上烤着吃;还有的操起一只羊腿,架在火上烧着吃……这下可救了命,不仅有吃的,还是高质量的食物。徐海东最后说:“幸亏了这群羊,才使我们坚持到了苏区。”
长征途中,由于路途遥远,各地条件不一,所以能获得的粮食也五花八门。从以上材料看,多数时间,有顿饱饭亦属不易,更不用提吃野菜、烧牛皮、嚼马粪中的青稞……长征是一次行军,同时也是对身体意志的严峻考验。
(本文作者为陕西省汉中市委党校教授)
本站编辑:杜瑞
主办: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晋ICP备15001143号-1
Copyright Shanxi Jinsui Culture Education &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9号院国投财富广场4号楼313/314 邮编:100073 电话:010-63395639/63395661 邮箱:sxjs9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