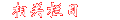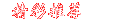
- 春节前又见老阿姨(02月06日)
- 基金会携手中青网传承晋绥红色文化(02月06日)
- 晋绥儿女的情怀(02月05日)
- 腊八节的思念(01月24日)
- “大寒”——林炎志大哥在京的一天(01月21日)
- 新年新风新气象(01月12日)
- 晋绥抗日老前辈牛文夫人晓民为烈士陵园捐树(01月05日)
- 新年贺词(12月29日)
- 贺晓明大姐向一二〇师学校赠送3D《中国地图》(12月28日)
- 岁末迎来晋南的客人(12月26日)
红四方面军的漫漫长征路(之七)
发布日期:2016-05-17 14:22 来源:中红网—中国红色旅游网 作者:胡遵远、李雨迪
红四方面军是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与红25军一样、主要诞生在我们安徽省金寨县。1935年10月开始长征,1936年10月结束长征。强渡嘉陵江、攻克剑门关,揭开了红四方面军万里长征的序幕。
八万雄师劲旅、浩浩荡荡西移,破坚阵、摧强敌,挺进川西北,最终在雪山脚下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但是,由于张国焘的阴谋夺权、导至红军一度分裂,红四方面军由此走上了一条漫漫的长征路。在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辗转长达一年之久,数万将士的鲜血洒满西北疆域……英雄的红四方面军最终用生命和鲜血战胜了恶劣的环境、反动的武装、错误的路线,夺取了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因此,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更加艰难曲折、更加悲壮震撼、更加可歌可泣,并且鲜为人知、充满传奇和神奇。特别是后来的西路军奉命渡河西征之后,与马家骑兵展开了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凯歌。
第七章 红四方面军长征中的巾帼英雄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4个师共2万余人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当时随军西征转战的女红军在30名以上。她们是:张琴秋、曾广澜、汪荣华、郑先如、黄新兰、林月琴、刘百兴、廖国清(彭素)、陈英民、王泽南、刘桂兰、周起义、陶万荣(苏风)、廖赤见、陈保青、何福祥、张茶清、陈槐英、廖镇芳、陈五洲、张大友、张正福、杨明善、施兰青、闵武慈、陈英等,其中有10多名女红军在入川途中、创建川陕苏区和长征以至参加西路军艰苦作战中牺牲、病故、失踪、被俘,或沦落为民。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从强渡嘉陵江起,就开始了旷日持久的长征。当时,撤至嘉陵江以西地区的红军主力部队、地方武装以及随军行动的地方干部和职工,总共约10万人。其中,女红军约有3000名。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渡过黄河的3个军,以及总部机关和直属团队,总兵力为2.18万人。当时参加西路军艰苦作战的女红军,总数仍有一千七八百人,与西路军总兵力的零数相当。其中,妇女抗日先锋团为一千二三百人,政治部前进剧团、供给部被服工厂(编有两个连)、卫生部总医院以及各军、师、团的部分宣传队员和医护人员,共四五百人。
在当时,随同红四军、红三十一军、红军大学女子连和红军总司令部机关及所属单位直接到达陇东和陕北的女红军,也有数百名之多。1937年,李坚真(时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在延安曾对斯诺夫人讲过一笔数字:“现在有600名妇女在延长县接受正规化的步兵训练,大部分是四川人。”
长征中,在红四方面军的滚滚铁流之列,这3000余名女红军随同万里转战,恰是红四方面军长征中独树一帜的雄伟壮丽景观——一部前所未闻的红色经典诗篇!正是:巾帼长征无所惧,生离死别谁人知?
陈真仁:举家长征,男女老少十一口 会宁会师,唯有九妹独一人
举家参加长征者,当数陈真仁一家三代十一口人,堪称红四方面军征战序列中典型之一。
陈真仁,原名陈锦云,陕西省宁强县大安镇烈金坝人,1919年出生,曾就读于汉中女子师范附属小学。她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九,是陈家最小的女儿,故有“九妹”之称。上小学时,就在大哥、二哥的影响和教育下,闹学潮,呼口号,撒传单,送密件,从事党的地下斗争。她的一家三代十一口成员是:
父亲陈大训,乡村绅士,时已年近六旬。大哥陈锦章,1924年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曾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艺术大学。1926年由上海回到家乡,组建中共宁强县支部,他为书记。后到汉中女子师范学校任教,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曾任中共陕南特委委员等职。二哥陈文华,中共党员,曾就读于汉中省立第五师范学校,历任该校党支部书记、中共陕南特委组织部长、书记,中共南城褒边区党委书记,红二十九军第三游击大队(后改称独立第三团)政治委员等职。三哥陈文芳,共青团员,中学生,时年不过20岁。大嫂(家庭妇女)、二嫂李泽生(中共党员,为共青团陕南特委组织部长、书记)、三嫂宁素梅(家庭妇女)。大侄女陈亚民(12岁)、二侄女汉兰子(4岁)、三侄女青梅子(不到半岁,为二嫂李泽生所生)。加上陈真仁,正好十一口人。
随同红军出发时,除母亲陈朱氏和两个已经出嫁的女儿留守在家外,这个家庭的全部成员,都踏上了艰苦的长征路。举家参加长征这一壮举,虽然不曾被载入红军长征史料丛书,可也堪称“一绝”!
1935年2月3日(除夕之夜),红四方面军以12个团的兵力发起陕南战役,于次日攻克宁强县城。广大群众在陕南党的领导下,踊跃参加红军,仅第三十军李先念部就扩充新战士1500余人。就是在这时候,陈真仁和她的三个哥哥、三个嫂嫂以及三个侄女,都加入了红军队伍。
红四方面军从陕南回师川北后,为配合中央红军长征北上的战略行动,即开始了历时24天的强渡嘉陵江战役。渡江之前,陈真仁一家在旺苍坝进行了整编分配:陈真仁的三个哥哥均被编入作战部队,从事政治宣传或地方群众工作;陈真仁和父亲、三个嫂嫂、三个侄女全被分配到被服工厂,这样也便于互相照顾。但在渡江以后的行军作战中,她的大嫂、二嫂都得了伤寒病,头痛发热,不吃不喝。二嫂怀里还揣个吃奶的青梅子,一路上更是苦不堪言。这两个女人和一个女孩,就这样被病魔折磨得掉队了,失散了,以至与红军失去联系。一天晚上,在一次紧急突围中,她的父亲和三嫂也相继失散,不知去向。直到后来,才确知这一老一小两人都在战斗中牺牲了。
陈真仁领着两个侄女到达土门后,她自己也染上了伤寒病,高烧昏迷,胡言乱语,接连躺了几天不省人事。这样一来,可把她的大侄女陈亚民害苦了,一个12岁的女孩子,既要守护生命垂危的姑姑,还要照看那个患有脱肛病的小妹妹。危难时刻,第二天就要向茂县进发,这个小不点儿的女孩子,无论如何也照顾不了姑姑和妹妹两个人,她必须从中舍弃一个。无奈之下,陈亚民将妹妹汉兰子托付给一个老婆婆收养。开始时,那老婆婆嫌其病重而不肯收留,陈亚民便悄悄把妹妹背到老婆婆门前,哄着妹妹睡着了,这才溜之大吉,扶着姑姑踏上了征途。1995年,时已72岁的陈亚民老人仍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我那时才12岁,我好狠心啊!我妹妹病成那个样子,没人照管。可是,我不扔掉她也活不了多久……”
长征中,陈真仁的大哥陈锦章、二哥陈文华、三哥陈文芳,都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谁也说不清道不明这三兄弟究竟战死在何时何地,或在何处安息。长征中这一家人,最后就剩下陈真仁、陈亚民两人相依为命,经历了三过草地的坎坷历程。
雪山草地,没有阻止住陈真仁、陈亚民的脚步。白龙江栈道、腊子口天险,都不曾拦住她们前进的道路。但在翻越达拉山即将进入大草滩时,陈亚民却掉队了。那一晚,陈真仁已经到了大草滩,她发现陈亚民没有跟上队伍,急得一夜都没有合眼。第二天早晨出发时,她一个帐篷又一个帐篷地寻找呼叫,还是没有见到陈亚民的影子。她不由抱头大哭:“我侄女掉队了!肯定掉在山那边了!”她要返回去寻找侄女,却被战友们阻拦住了,遂被人扶着一步步向哈达铺走去……
高耸入云的达拉山,乃是长江、黄河的分水岭,同时也是陈真仁、陈亚民人生命运的分水岭。他们一家三代十一口人,最后坚持到达陕北者,唯有陈真仁一个人。陈亚民这个12岁参加长征的女孩子,一路上也不知爬过多少高山峻岭,却在漫漫征途的最后一道山上跌倒了。从达拉山到大草滩,就那么一天路程,她却没有跳过“龙门”。后来,她走到一个叫麻石川的地方,被一个老婆婆收留下来,装哑巴休息了三、四个月,脚才好了。再后来,她便挨门讨饭到了哈达铺,给一户人家打短工,借以糊口维生。谁知这户人家心太狠,居然不顾先头红军在当地留下的政治影响,将她领到岷县一带卖给了别人。她在岷县整整待了八年之久。……抗日战争胜利后,陈亚民曾想逃回家乡,竟被主人打得奄奄一息,抛弃于荒野,幸好遇见一个到岷县办事的宁强县老乡,这才将她从野地里搭救过来,并雇人抬着她走了20多天,终于回到了宁强县烈金坝。曾经人丁兴旺的陈家大院,此时早已人去屋空,彻底地破落了、衰败了。迎候这个长征中掉队归来的孙女者,仍是当初要她留下做伴而没有留得下的老奶奶陈朱氏。生离死别十年整,如同一场做不完的噩梦!
长征中,陈真仁在红四方面军总部卫生所当护士时,跟红军名医傅连暲恋爱了。1936年10月10日,她在会宁县城参加了胜利会师大会。之后,陈真仁和傅连暲到达同心城,领导上才批准他们正式结婚。
陈真仁的48年军旅生涯,完全献给了军队的医药事业,直至离休。1955年她被授予上校军衔,傅连暲则被授予中将军衔。
李开英:生作人杰,劝郎戒烟当红军 死为鬼雄,自有故知祭英灵
李开英家在川北通江县城以西的鹦哥嘴,加入红军时30多岁,精明能干。当地有句口头禅:“要吃通江饭,婆娘打前站。”李开英就是一个事事处处都打前站的“川嫂子”。1932年冬,从红四方面军入川时起,李开英就成为一名响当当的女中英豪,名声传遍了通江城乡。
苦难岁月,川北穷人深受鸦片的毒害,鸦片当时已成了一大祸患。有不少青壮年男子因为吸食鸦片烟,弄得倾家荡产。李开英的丈夫老鲜就是一个大烟鬼。
红军来了以后,李开英才感到有了盼头。她是村苏维埃的妇女委员,积极动员和组织本村妇女参加打土豪、分田地,帮助红军运输粮草。她儿子鲜炳文也参加了儿童团,扛着红缨枪站岗放哨,盘查路条。县、区两级苏维埃政府,当时还设立了戒烟局、戒烟所,首先号召穷苦农民实行戒烟,坚决行动起来与烟毒恶魔作斗争。李开英积极响应号召,特意跑到通江县城的戒烟局,以平价购买了几包戒烟丸,拿回来分配给患有烟瘾的穷苦百姓,剩下一些给了自己的丈夫。然而,丈夫吃了戒烟丸丝毫不顶用。
无奈之下,她又把丈夫送到红军开办的戒烟所。月余后,丈夫终于戒掉了恶习,脸上有了血色,身体逐渐康复起来。7月间“扩红”时,老鲜连家都没有回,从戒烟所直接参加了红军。
李开英从此名扬乡里,成为当地的一名妇女积极分子,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妇女踊跃参加红军的热潮中,她按捺不住一个新党员的赤诚之心,领着独生子鲜炳文一起参加了红军。由于她是党员,阶级觉悟高,表现好,当时就当上了排长。她儿子也跟她在一起待了一年半之久,个头长高了,身体强壮了,赶到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时,年已十四、五岁的鲜炳文这才被调到红九军当勤务员。
长征开始后,李开英当上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妇女工兵营二连政治指导员。红四方面军南下转战期间,妇女工兵营缩编为两个运输连,分别由营长林月琴、政委王泽南兼任第一、第二连连长。王泽南虽比李开英年轻几岁,但她小时缠过脚,走路摇摇摆摆的,很不利索。每次执行运输任务时,大都由指导员李开英带领一两个排,配属各兵站运输粮食、物资,或到总医院驻地抬运伤病员。长征中,她先后两次翻越大雪山,三次穿过茫茫水草地,历尽爬雪山过草地的艰难困苦,同时也更加锤炼了她的革命意志和战斗勇气。
1936年8月,红九军围攻岷县县城,李开英的丈夫老鲜在给二郎山阵地部队送饭时身负重伤。老鲜时在红九军某连当伙夫班的班长。李开英本想前往探望,因当时奉命到妇女抗日先锋团担任指导员,而没能遂心如愿。是年10月初,红军撤离岷县以后,她听说留在水磨沟的红军伤员大都被鲁大昌部给枪杀了、活埋了。此后,她再也没听到过丈夫的消息,只有把整个心思操在儿子鲜炳文身上。
李开英随妇女团渡过黄河后,参加了比长征更为艰苦的西征作战。西路军失败后,李开英与众多红军姐妹一起,成为马家军的俘虏。起初,她被押在张掖以南100多里地的花寨子,随后被押往青海西宁。押解途中,有一天到达扁都口附近的炒面庄,敌人指定李开英、李文英跟着何福祥到河边背冰块化雪水做饭吃。在此时刻,何福祥发现无人监视,天也黑了,果断地打了个手势,三人趁机逃跑而去……
何福祥是来自大别山的女红军,湖北红安人,1929年16岁时参加红军,被俘前在妇女团当营长。她个头高大,体格强壮,被女友们称为“大洋马”。李开英、李文英两人就跟着这位老营长一边乞讨一边赶路,沿着祁连山北麓的戈壁滩,一步不停地向东走去。她们的目标是:要革命,向东走,过黄河,回陕北。但想不到的是,她们在路过大马营时,李开英却惨遭不幸……
一天,李开英自告奋勇先走一步,为两位难友打前站。当她向一个牧羊老汉问路时,那老汉一听口音不对,便吹起了口哨,呼叫出两条护羊狗,朝她猛扑而来……等到何福祥、李文英赶来时,发现李开英被咬得浑身是伤,血肉糊糊的一截肠子也被狗扯了出来。危急时刻,她俩把李开英抬到附近的一个土窑洞里,进行擦拭和包扎伤口。李开英原本疼痛难忍,可她却说腹内饥饿,叫给她讨点吃的,弄点水喝……
等到何福祥、李文英把吃的喝的弄来时,却发现李开英把随身所带的一块大烟土吞了下去,正好毒性发作,口吐白沫,脸色发青,浑身搐动不止,气都喘不过来了。何福祥把她抱在怀里,边哭边说:“大姐,你不该这样作贱自己呀!”忙叫李文英往她嘴里灌水,指望她能把大烟吐出来,李开英却把牙齿咬得死紧,撬都撬不开。半晌,李开英才吐出几句话:“疯狗咬了好不了,也活不了。你们赶紧朝东走,别受我的拖累……”沉了一会儿,她又喃喃地说:“日后见到我儿子,他叫鲜炳文,在九军当勤务兵,就说……就说他娘革命到底了……”
规劝丈夫戒烟当红军的川嫂子,而在遭到恶狗咬伤以后,自知伤情严重难以活命,遂将发给她当做路费使用的一块烟土,于危难关头结束了自己的性命。她不知道,她所怀念的儿子鲜炳文,早在跟随红九军西征作战时就壮烈牺牲了。
1984年,与李开英同一个故乡的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傅崇碧将军曾在《难忘的故乡人民》中这样写道:“记得我们通江县鹦哥嘴,有个女同志叫李开英,家里很穷。红军来了以后,她带头组织妇女参加打土豪、斗地主,是村苏维埃的积极分子,后来又入了党。在‘扩红’中,她先是动员丈夫参了军,自己又带着才十二、三岁的独生子一同参了军。儿子在部队当通信员,她在总部做后勤工作,后来还当上了排长、指导员。在西路军的艰苦血战中,她一家三口全都英勇牺牲了……他们的英雄事迹和革命精神,将永远受到怀念!”
曾广澜:母女二人,西行长征复西征 作战被俘,有幸回归大本营
曾广澜出生在江西省吉安县白沙乡曾家村,192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她的兄长曾山就将她从吉安领到南昌,叫她与一位素不相识的湖南人扮成夫妻作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是年11月间,二人居然“弄假成真”,正式结为一对志同道合的革命夫妻。丈夫就是蔡申熙,湖南醴陵县人氏,中共党员,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时任中共江西省委军委书记。
1930年,蔡申熙奉命率部向北转战于鄂豫皖苏区,与红一军合编为红四军。此后,蔡申熙就落脚于大别山区,历任红四军第十师师长、彭杨军校校长、红二十五军军长等职。1932年,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后,蔡申熙奉命奔赴皖西前线指挥作战。同年10月9日,蔡申熙在河口镇战斗中负伤,不幸逝世。
对于蔡申熙,徐向前、刘伯承两位元帅都有过很高评价,就连张国焘也不得不承认蔡申熙是“公认的一位老谋深算的战略家,他的死亡使我们大为震悼”。由于情况紧急,当时也顾不上举行悼念仪式,曾广澜和红军指战员们一起,以泪水伴着黑土就地掩埋了蔡申熙这位年仅27岁的红军将领!
红四方面军西征后,曾广澜擦干眼泪,挺起身子,背着刚满三岁的小女儿,急急忙忙也踏上了征途。母女俩一路上过丹江、越秦岭,再渡汉江、翻越大巴山,随军西征转战3000里,进入四川。是年12月,部队到达川北站稳脚跟以后,这才争取到半天时间,由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主持,为蔡申熙举行了追悼大会。1960年,曾广澜还曾撰写过一篇《回忆申熙同志》的文章,以志纪念。
红军入川不久,曾广澜就奉命组建妇女武装,她跟“假小子”陶万荣一起,并肩扛起红四方面军第一支妇女武装的战旗。1933年3月,妇女独立营在通江县城成立,营长陶万荣,政治委员曾广澜。全营总共300余人,编为三个连队。除营长、营政委和部分连排干部外,大都是来自大巴山区的穷姐妹、苦丫头、童养媳。全营战士,是清一色的巴山女红军。
1934年3月,妇女独立营扩编为妇女独立团,曾广澜为第一任团长兼政治委员。后来,她还担任过中共巴中市委书记、省苏维埃政府邮政局局长、西北联邦政府裁判部部长等职。长征中,她跟女儿蔡萍迹相依为命,经历了两过雪山、三过草地的艰难跋涉,受尽了风霜雨雪之苦和饥饿疾病的折磨。1936年夏天,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北上时,母女俩靠着一匹小青马,经过20多天的艰苦行军,越过水草茫茫、遍地泥泞的大草地,随军到达包座地区,暂时休整了数日。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曾广澜又被调回红四方面军妇女抗日先锋团担任特派员。到职后,她便领上女儿蔡萍迹,随同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一起渡过了黄河,踏上艰险而又悲壮的征途。
西征失败后,作为团的领导和指挥核心,最后坚持在一起的就剩下曾广澜和团长王泉媛、团部秘书李开芬,以及另外两、三名女战士了。她们当时已弹尽粮绝,精疲力竭,走投无路,陷入绝境。白天,到处都是搜山围攻的敌人,她们只能躲在山洞里、树丛中、悬崖下,既不能烧火冒烟,也不敢寻找吃食,甚至连咳嗽两声都得捂住嘴巴。为了不被敌人搜到活捉,只能采取捉迷藏的方式东躲西藏,与敌巧妙周旋。
这天傍晚,一拨又一拨的搜山敌军撤回营地以后,王泉媛等人才摸下山去,找到一处独户人家,以大烟土换了些食物,暂且得以充饥。她们就便了解了敌情、道路,连夜又出发了。她们决定先走出祁连山,然后再沿山向东走,回归陕北。几个人奔走了大半夜,天将亮时,怕发生意外情况,只好进行隐蔽躲藏。王泉媛发现半山腰有几孔破旧窑洞,就选定哨位安排哨兵,然后招呼同志们进去休息。
谁知刚睡下一会儿,天就亮了。睡梦中,也弄不清是谁喊了声“敌人”,便不约而同地惊醒起来。这时,恰好就有几把明晃晃的马刀堵在了窑洞外边……原来,哨兵也在哨位上睡着了,被敌人一刀砍死在地。她们一行六七人就这样做了俘虏。被俘后,她们被押送到张掖韩起功的司令部……
参加西路军艰苦作战的妇女独立团1200多名女战士,除部分英勇战死外,绝大部分被敌人俘虏。团特派员曾广澜和她的女儿蔡萍迹后来之所以获释,实属侥幸。
曾广澜母女俩是1937年9月22日由武威抵达兰州的,同行者还有回民支队司令员马良骏、骑兵团长徐明山以及李保安、石建武、祁骏山等人。9月26日,他们一行15人(其中有从青海归队的刘瑞龙、魏传统、吴建初、丁世芳等人),由兰州乘汽车回归延安。
从1929年冬到1937年秋,曾广澜和她的女儿蔡萍迹经由江西、江苏、湖北、安徽、河南、陕西、四川、西康、甘肃、宁夏、青海等省,足迹踏遍了半个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曾广澜由延安回到吉安,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0年被捕入狱,与党失去组织联系。出狱后,仍坚持革命斗争,于1948年底在吉安等地组织发动群众夺取反动武装枪支,为解放大军保住了大批粮草。1950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吉安专区妇联副主任,1968年去世。
刘伯承、汪荣华夫妇对蔡申熙、曾广澜夫妻二人分别有一段回忆和评语。刘伯承在1960年10月1日的亲笔题词中写道:“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与蔡申熙同志在周恩来同志主持的军事委员会之下工作。他给我的印象是:忠诚勇敢,工作认真……以后闻他率军过了长江,入大别山与鄂豫皖红军会合,在反蒋介石围攻中英勇阵亡。蔡申熙烈士永垂不朽!”汪荣华则在她的《征途漫忆》中写道:“1935年春,省委转移到广元县旺苍坝时,我调任省苏邮政局当副局长……后来,曾广澜同志也调来了。她是一位纯朴、诚实、正直的好同志,比我年纪大一些,我们相处得很好。她在1968年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这位老大姐虽然已离开我们十多年了,但我一直怀念着她!”
戴觉敏:革命家庭,经风见霜枫叶红 生离死别, 万里远征见证人
戴觉敏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创始人之一戴克敏的胞妹,家在湖北红安县七里坪戴家村,生于1916年农历八月初五。
父亲戴雪舫是位教书先生,在五四运动影响下,积极从事新文化运动,与董必武交谊甚厚。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麻城县委书记、鄂豫皖苏区列宁高等小学校长等职。1932年,第四次反“围剿”之初,鄂豫皖苏区首府新集遭到敌机狂轰滥炸,学校大门也被炸弹炸塌,戴雪舫为掩护学生转移,不幸被弹片击伤肺部,被抬到箭场河红四方面军总医院进行手术治疗,两天后,终因抢救无效永别人世。经总医院领导批准,由戴觉敏(时在总医院当护士)亲自陪送父亲的灵柩回到七里坪戴家村进行安葬。
哥哥戴克敏(又名戴道规),1924年18岁时考入武昌第一师范学校,在董必武的影响下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他参加领导了著名的黄麻农民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和吴光浩率领72名成员,转到木兰山开展游击战争,任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党代表。1928年后,历任红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党代表、红一军第一师政治委员、红四军警卫团团长、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政治委员等职,率部参加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徐向前元帅生前曾念念不忘这位红军战友,说戴克敏在红军中威信很高,“可以说是大家的表率”。令人痛心的是,他不是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而是被张国焘加以“改组派”的罪名于1932年夏天错杀在新集,时年仅27岁。
在那血与火的岁月,戴觉敏一家共有14人参加革命,当时已有10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她的十叔父戴先诚,在黄麻农民暴动中牺牲;二伯父戴先治、三伯父戴伯先、四伯父戴先致,先后于1928年或英勇战死,或被敌人抓捕杀害;堂兄戴道溥1929年被敌机炸死;堂兄戴道高、戴道深1930年在作战中牺牲。她的父亲戴雪舫是第八个牺牲者,哥哥戴克敏是第九位为革命捐躯的。与她同时参加红军护士班的堂妹戴醒群的父亲戴叔先(即戴觉敏的八叔父),时在总医院中医分院当院长,也在1932年“肃反”中被错杀,成为第十个捐躯者。
1932年是多事之秋,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转战到了四川。危急关头,另一名堂兄戴道彩随红四方面军入川而去;戴觉敏、戴醒群姐妹二人因当时来不及随军行动而被留在了大别山里,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后来,她们都成为红二十五军战斗序列中的白衣女战士。
红二十五军在坚持鄂豫皖根据地斗争的两年间,戴觉敏所在的原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已分成若干分院,连同伤病员一起转移到天台山、老君山的密林里,继续坚持医疗护理工作。
1934年11月16日,戴觉敏随同红二十五军出发长征。当时,随军长征的有七名女护士,正好编成一个班,故有“七仙女”看护班之称。
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由长安县沣峪口继续长征北上时,“七仙女”班班长曾纪兰牺牲在宁陕县境,戴觉敏等六名女护士,全都随军行动。但在北过渭河以后,女护士曹宗凯却躺在担架上含冤死去……
长征到达陕北后,“七仙女”班剩下的五个姐妹,除张桂香与戴季英已结婚外,周少兰(后改名周东屏)与徐海东、田希兰(后在陕北病故)与钱信忠、余国清(后改名余光)与李资平、戴觉敏与饶正锡结婚。建国后,周东屏、戴觉敏、余国清分别成为大将、中将、少将夫人。
解放战争时期,戴觉敏身在西北战场,却无时不在惦念着大别山里的亲人。新中国成立时,戴觉敏和她的丈夫饶正锡远在西陲边城工作。全国解放了,革命胜利了,远离家乡十五、六年了,她能不想家和思念亲人吗?巍巍大别山,红军战士的摇篮,那里有她时刻牵挂的母亲石兰英,还有她哥哥戴克敏的妻子曹吉阶,以及哥嫂的亲生骨肉戴曙光。
1950年冬天,戴觉敏经由北京、武汉回到故乡寻找亲人。她没有找到她的母亲,只见到几位婶娘,这才听说母亲石兰英十多年前就饿死在流离乞讨的路上。至于她的嫂子曹吉阶、侄女戴曙光,虽经多方打听寻找,却一无所获。
戴觉敏跟随丈夫调到北京后,1955年的一天,她在探望来自大别山的中共中央委员郑位三时,终于获得侄女戴曙光的下落,惊喜之余激动不已。戴曙光,这位大别山革命人家的革命后代、戴克敏烈士的唯一女儿,她还活在人世,当姑姑的真是喜出望外。
这年的金秋十月,戴曙光被姑姑邀到北京。20多年不曾相见,侄女已是26岁的少妇,并生有一儿一女。丈夫名叫郭德辉,是个本分农民,家在麻城县中馆驿郭家洼村。姑侄二人相会时,戴觉敏才晓得寡嫂曹吉阶的遭遇更加悲惨:苦难岁月,嫂嫂背着三四岁的女儿于黄麻边界流浪乞讨,被保长绑架、贩卖到麻城县余家湾,迫使她做了农民余万里的妻子。女儿亦改名姓余,叫余影香,后恢复原名戴曙光。遗憾的是,嫂嫂曹吉阶已于1953年清明节后病逝,姑嫂二人最终也没有见上一面。
1984年,戴觉敏老人在向笔者口述了她一家人的情景后说:“我是我们一家的幸存者。像我们这样的革命家庭,在大别山区又何止我们一家,有成千上万啊!我们红安县的革命家庭,的确很多很多……”
(本站编辑:杜瑞)
主办: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晋ICP备15001143号-1
Copyright Shanxi Jinsui Culture Education &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9号院国投财富广场4号楼313/314 邮编:100073 电话:010-63395639/63395661 邮箱:sxjs9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