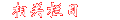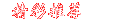
- 有这么一批《晋绥日报》的传承人(07月10日)
- 浇开中朝友谊之花(07月09日)
- 有一种记忆叫怀念……(07月08日)
- 有份爱心来自大唐(07月04日)
- 播撒慈善的种子(06月28日)
-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大力弘扬吕梁精神(06月21日)
- 悼念王军大哥(06月11日)
- “土窑泥坯”到军博(05月28日)
- 晋绥情怀和“智慧乡村”(05月23日)
- 2018年基金会工作回顾(二)(05月14日)
庚申忆逝(1—3)
发布日期:2016-01-25 12:09 来源:《庚申忆逝》 作者:张稼夫
前 言

张稼夫
自从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大力进行了拨乱反正的工作,到六中全会已大见成效,许多被混淆了的是非曲直问题,得到了纠正,保证了我们党能够继续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前进。这是一项关系到我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成败的大事,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是应当大书特书的。在十年动乱期间,被混淆了的事物,既有现实问题,也有历史问题,既有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也有个人的功过毁誉问题。我亲身体会到坚持实事求是,既需要理论、见识,也需要勇气、胆量。在“文化大革命”中别有用心的歪曲事实者不乏其人,无知和幼稚的受骗者也颇为众多。对于后一种情况,可以谅解,然而谅解不能帮助受骗者觉悟过来。这个情况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使后来者了解革命前辈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从中汲取教益,少走弯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经历至今萦绕在心头。一批又一批的外调者使得我应接不暇,写了许多证明材料。诸如,山西的青年抗敌决死队,国民兵军官教导团,战地动员委员会,十二月事变,民族革命大学等许多问题,竟然成了糊涂帐,都来调查。其实,那是我们党在山西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产物,局外人是难以理解的。例如:仅仅为了一个山西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的问题,外调者问:牺盟会是不是反革命组织?我回答:不是反革命组织,而是革命组织。外调者又问:牺盟会的会长是不是阎锡山?我回答:不错,阎锡山是会长。我的这种回答,不要说红卫兵听了要吃惊,就是不了解山西情况的参加革命较晚的干部也不易理解;反革命头子居然是一个革命组织的领导人,这真是不可思议!但是,历史事实确是如此,不能改变。为此,我对外调者,不得不仔细地介绍抗日战争时期山西的形势、特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牺盟会以及其他组织的产生及其发展的历史,还要特别地反复地说清楚,阎锡山只是名义上的会长,实际主持工作的人则是共产党 员薄一波、牛荫冠等同志,从上层 到基层大部或者基本上是共产党 员掌握了实际领导权,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绝大部分外调者听了我的介绍,看了我写的证明材料,是满意的;有的甚至说,好象上了一堂政治历史课,气冲冲而来,欣欣然而去。与此同时,我又被迫交待我的历史,这就使我对于走过的道路作了一番又一番的回顾;本已模糊的某些历史情况,经过回忆,又历历在目。而那些历史情况又正是目前的年轻一代所不了解的。由此,我就想到,应当向新的一代介绍革命斗争的历史,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前两年,出于一种阶级友谊和政治责任感,我写了怀念林枫同志的文章。有些同志看了文章以后,劝我把个人的经历,特别是从太原失陷到晋西事变的这一段经历也能忆述一下。因为从领导角度能够讲述清楚这段情况的人,已经为数不多了,并且通过个人的经历把当时党的工作的某个侧面反映出来,是有意义的。于是,由于这些同志和现代史研究所同志的一再鼓励,我就不揣浅陋,写上几页,聊胜于无吧。
我接触马克思主义较早,“五四”时期就开始阅读马克思著作,但是直到一九二七年才参加中国共产党,其原因是我少年时期形成的固执性格所致。我不理解的我不信仰,我追求的是透彻的理解,我想,脑袋长在自己肩膀上,要自己去思考,不应盲从。这在实际上也发生了一个标准问题,即自以为理解的,正确的,并不一定都是真理,这需要实践的检验;不过我的性格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我对我已经选择的信仰——马克思主义,从不动摇。我对党是忠诚的,即使在我和党失去联系的时候,或者在我们党的事业遭受挫折的时候,也决不动摇。我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这大概也就是我可以向读者提供的一点礼物了。
我写这篇材料的本意是想总结一下我自己所走过的道路。哪些作对了,哪些作错了,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加以叙述和总结;不文过饰非,不隐恶扬善,不为自己树碑立传。待这个材料写完,又感到没有多少可取的经验,深感抱愧。在写作过程中,从童年写起,是为了说明我的性格形成的过程,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在写作的方法上,只写我经历的事物,听来的事不写,有些非写不足以说明问题时,也要少写。我不越俎代庖,甚至掠人之美。因此,从一个地区的工作情况来看,我写的这份材料可能不连贯,不全面,那也只好宁付阙如,也不强不知以为知了。
是前年(一九八〇年.庚申年)开始写了个提纲,打了个腹稿。所以就把题目定名为《庚申忆逝》。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中共山西省委、太原市委、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李新、聂元素同志和有关的一些同志的鼓励和支持。我的写作过程是这样的:一九八一年六月我去到太原,向山西省文联借调了李束为同志,向太原市委宣传部借调了黄征同志,首先由我口述录音,再由黄征同志整理成文字 资料,最后由李束为同志加工写成为本文的征求意见稿。在初稿打印以后,许多同志又提出修改意见,有的同志还提供补充材料。今春我又根据这些同志的意见,请黄征同志来京,帮助我在中央档案馆和北京图书馆查阅了若干必要的档案、文件和报纸。力求本文所述往事的时间,地点和情况,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校正我自己记忆中的失误之处。今年五月,我得到云南省委的同意,约请李束为、黄征同志来到昆明,把这个稿子最后修订了一遍。在修改的过程中,有一些地方在文字上,曾经过王修同志的加工。所以我的这篇文章的写成,既包含了李束为和黄征同志的大量心血,也得到了中共山西省委,云南省委和以上所有同志的支持、鼓励和协助,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在这一修订稿写完以后,我自己为了慎重起见,将全稿从头至尾,又认真地审阅了一遍。 当我读到第十四段我将离开晋西北去延安时,想在后边再增加一点,将我自己从一九二七年四月入党以来,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的学习和锻炼的过程,回顾和总结一下。未料我这一写,就停不下笔来;当我写到若干“以身作则”地对我进行过党性修养教育的同志,特别是写到抗日以后和
我相处最久的林枫同志时,于是我就不得不写长了许多。因此,我自己就决定将它另行列为一段,便成为这一稿中的第十五段。
张稼夫
一九八二年七月于昆明
一
公元一九〇三年十二月五日,我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西北安村的一个中农家庭里。
西北安村是一个不足二百户人家的小村子,离县城四十五里,距交城县城只有十五里,处于晋中平原的西侧,背靠吕梁山,面向汾河。这里的土地虽然平坦,且得汾水冬灌之利,但土地贫瘠,生产方式落后,农作物产量很低,多数农民生活贫困,文化也很落后。由于依靠土地难以温饱,许多人家不得不出外谋生,有的远走关东、蒙古,赚些“外汇”以维持生活。
我的祖父张秉让也是个走口外的。他在十四、五岁上,因为家里生活困苦,便跟随他舅父家(文水县武午村)的人到了库伦,就是现在的乌兰巴托,在一家杂货铺里当店员,学做豆腐和酿酒造醋的手艺。由于他的人缘好,干活也肯出力,后来在这个小铺子里熬下了一个身份股子,到年底,除了饭钱还能剩下一些银子,寄回来接济家庭生活。这样,家境有了一些好转,又加之省吃俭用,便买了几间房子和二十亩土地,连同原来的八亩沙滩地,就有三十来亩,生活可以勉强维持了。
我父亲张鸿基是个独生子,他四、五岁的时候,害了一场大病,大夫在他哑门穴上扎了一针,从此,病好了,父亲却成了聋哑人,铸成了终身痛苦。母亲是个童养媳,她出生不久,外婆就去世了,因为家里太穷,养不活她,就把她用布被包上放在大辛村(属交城县)一家财主的大门口,被捡回去养大当丫头使唤。后来,这家人败落了,外祖父才把她认领回来。母亲十多岁就到了我们家,她从小当丫头挨打受骂,当了童养媳以后,家庭生活并不宽裕,父亲又是聋哑人,精神受到极大刺激,终日郁郁不快,逐渐形成歇斯底里的特点,经常无端的打骂我们,甚至以跳井来吓唬我们。我们兄弟姐妹心里实在感到委屈。那时,我们不懂事,不理解母亲内心的痛苦,不去安慰她,常常一跑了事,至今回想起来,深深感到内疚。
我的母亲生了我、我的两个姐姐和三个哥哥一个妹妹共七个孩子。我们的家庭是个不幸的家庭,我的两个姐姐、大哥和三哥都未成年,先后得病死了。二哥从小就有些傻,家里人不喜欢他,我便成了全家的宝贝。祖母、母亲怕我也得病死了,找了个瞎子给我算命,说要请十三太保,才能保住性命,于是约请了十三个“干老子”,其中有活人,也有庙里的神像,如土地爷之类,甚至还有狗,因为狗最恋家。打也打不走,是个很得力的太保。每逢过生日,要在我的脖子上拴十三根红线绳绳,耳朵上扎了个眼子,还要挂小银锁,叫做“假妮子”。一直到我十二岁那年才开了锁,不戴了。这些迷信的事情在旧社会是惯见的,也可以想见我们的家庭,以及西北安村那个环境的精神面貌了。
我的外祖父名叫岳庆余(交城县辛南村人),是个以编柳条筐子谋生的手艺人。他的手艺很高,编下的筐子远销祁县、太谷等地。他虽然是个文盲,却很会讲故事,他给我讲得最多的是关于葫芦王的故事。葫芦王是当地农民起义军的领袖,曾经和李闯王的部队一起攻打太原。李白成失败以后,他仍然在吕梁山坚持斗争,劫富济贫,深得群众的拥护。他讲故事有声有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我开始懂事的时候,辛亥革命爆发了。满清皇帝被赶下了龙座,建立了中华民国。当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山西的同盟会员策动当地清军管带姚以玠等起义,打死了巡抚陆钟琦,成立了督军府。那时,原为清军八十六标标统的阎锡山混入革命队伍,窃取了革命成果,当了山西的都督。接着,他又投靠窃国大盗袁世凯,为复辟帝制效劳;他凭仗他在山西的特殊地位,统治山西长达四十余年之久,这真是对于历史的嘲弄。后来山西一些有点进步思想的人,就形成一种“反阎派”,还有各种政治倾向的人,也都是反阎的。
我还记得,小时候念的《革命三字经》,书的横眉上画的是孙中山、黄兴等人的头像。课本是共和、排满的内容。奇怪的是,当时也有保皇党康有为写的《国贼孙文》的小册子,和《革命三字经》并行不悖,形成鲜明的对照。我们那个小村子也受到这些影响,民主与封建,革新与保守的斗争也就逐渐激烈起来。村里有个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名叫张鹏举,有钱有势,豢养着好多车马,雇着好多长工,经租很多土地,是个经营地主,他常常为了争水浇地和邻村或村里的人们打架,仗势欺人,横行乡里,人们敢怒而不敢言。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终于跳出一个对手。这个对手叫张序龙,人们称他为三老爷,或关东三。三老爷是个贫农,辈数大,为人正直,下过关东。村子里有打架斗殴、家庭纠纷等事,请他出来排解排解,就解决了,所以在群众中颇有威信,起着族长的作用。三老爷对于张鹏举的横行霸道自然看不惯,在群众的支持下,站出来,代表本村群众和他斗争。到县城打官司,和张鹏举打架,吃了亏,挨了打,也不灰心,不让步,终于把他斗倒了,而且把他赶出村去,不许回村。这件事大大鼓舞了穷人的斗志,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作恶的人是可以斗倒的。
但是三老爷并不是民主势力的代表人物,他虽然代表群众打倒了恶霸张鹏举,热心公益事务,名声也好,只不过有些正义感罢了,并不具有先进的民主思想。具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的人则是张晋瑜,子玉。张子玉长期在外地生活,和参加辛亥革命的人物以及日本人有接触,在天津大德玉汇兑庄工作,常回家住。每次回来,总是西装革履,在家里养种奇花异草。他带回一个留声机,装上一个大喇叭,放唱片,哇哇响;又经常骑一辆自行车在村里村外走来走去,铃子哨啷响。他还会用电池和铜烟袋一接触就嗤嗤响,放火花;他对人们说,天上的雷电是阴电和阳电碰到一起引起的。村里人听了觉得很新奇,很有趣。他不信神,从天津写信来劝大家把盖庙的钱用来办学堂,并向人们宣传自然科学知识。虽然他对人很热情,但是人们都叫他“魔鬼”,因为他不信神,还想打掉神像。张子玉的一系列言行,引起极大反响。尽管他被认为大逆不道,并且最后死在保守势力的斧头之下,然而,在许多人的心里却点燃了民主与科学的火花,播下了追求进步的种子。他留给我的印象也是非常深刻的。
就是在这种封建和民主、保守和革新的激烈斗与的环境中,度过了我的童年。新的和旧的东西经常在我头脑里打架,生活向我提出了许多我不理解的新问题;我思索,希望有人引导我找到明确的答案。这就初步养成了我一生中喜欢思索,凡是我尚未理解的事情,不肯轻易盲目接受的性格。
二
在我们这个目不识丁的文盲家庭里,我成了精心栽培的苗苗。他们寄希望于我的,并不是知书达礼,作官为宦,更不是希望我成一个造福于人民的政治家;他们既无这种奢想,亦无这种远见,而只只不过是期望我成为一个能写会算,养家糊口的买卖人,就象我们的邻居那样,从口外带回银钱和布匹,那就是最好的理想了。所以,在我入私塾以前,母亲便教我识字。说来也真奇怪,她一字不识,但教子心切,便从识字的邻居那里一字一句的学来,然后教给我,日积月累,我竟从母亲那里学会了《百家姓》、 《《三字经》和《千字文》这类启蒙小书。当我进入私塾那天,母亲特为我打了一个烧饼揣进我的怀里,烧饼上还用簪子扎七个孔,这大概是洞开七窍,顿开茅塞的用意吧。
我的第一个启蒙教师叫韩仲禄,交城县城头村人,是个清朝末年的秀才。老婆死了,没有儿子,两个女儿出嫁了,他一人到我们村里教私塾。他爱喝酒,喝得高兴了,就给人们讲故事。聊斋、三国、水浒、神、鬼、狐、仙无所不谈,讲得有声有色,在我的幼小心灵上幻化出若干的稀奇古怪的社会历史现象。现在想来,这大概和念书本一样,听讲故事也是一种启蒙教育吧。当时我们的课本是《论语》、《孟子》之类,不分句逗号的古文木版书。上课时,老师先用朱砂笔点句,然后让学生去念,去背,也不解释是什么意思,越念越糊涂。我对这教法很反感,我对老师说,不懂得书上的意思,我怎么能背得出呢?老师嫌我多嘴,就打手板,我挨了打还要和他讲道理。老师也没办法,只好给我讲,我的语文和古汉语的基础就是这样“打”下的。后来我才知道,讲书是要交开讲费的。由于我学习认真,韩老师竟然偏爱我,免费开讲,并且多次表示:“回也视予犹父也”,把我当儿子看待,很下番辛苦。我在那里学了四、五年,《四书》、《幼学》、《诗经》都念了。到了民国四年,文水县的一个高小毕业生,分配到我们村当老师。韩老师只得回到城头村继续教私塾,我也跟他到城头村学习。韩仲禄老师有个侄子名叫韩壁,号玉人,交城县高小毕业,失业在家没事干,和我很要好,常常教我学习各种新学科。他不信神,不信鬼,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他到庙里把财神爷的胡子拔下来,还打耳光。说你这个财神爷不公道,为什么只让富人发财,不让我发财?他还把庙里的小菩萨搬回来,夜里拴在尿盆上。我是又吃惊,又开心,感到新学比旧学好。我在这里只学习了一年。这短暂的一年里,韩壁给我的影响很大,是我的头脑里无神论思想初步确立的一年,
一九一四年,文水县成立了甲种实业学校,这是我们县成立的第一个仿效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科技学校。校长是个留日学生,教员也有很多是留过日的。学校里设农、工、商科。那时,辛亥革命不久,旧的东西在人们的头脑里还很深,许多人对洋学堂不了解,几乎没有人肯送自己的孩子进这个学校,于是采取了拔壮丁的办法,每百户选送一个学生。有的村子没有人去上学,就在城里雇人顶替。我们村没人愿意去,我因受韩璧影响,自己要求去,经三老爷同意选拔去的。上学全部是村里公费,除了吃饭,还在一个小铺里立了一个户头,打煤油、买点心不用花钱,记上帐由村里付款。这比拔壮丁优厚多了。
我是在一九一七年进甲种实业学校的。那时正是智力突飞猛进时期,接受能力很强,很快地适应了学校的环境。这个学堂和私塾大不相同,完全是新东西。立正、稍息,学军事体操,打野外,数理化,专业学科,还学英语。新鲜的很啊!但是好事多磨,文水县农会的会长高叙宾企图把这个学校置于他的控制之下,成为培植私人势力的阵地,想方设法破坏这个学校。还说什么学校办的很糟糕,招了些烂炭猴儿学生,不成个体统。我们的老师就发动学生闹学潮,把农会砸了个稀巴烂。农会会长雇上人,扬言要和学校打架。我们有位老师名叫张仰仁,是陆军测量学校毕业的学生。听说农会要打架,就穿上军装挎上洋刀,带上手枪,准备和农会会长打架,把农会会长吓住了。可是,到了暑假,高叙宾趁机夺了权,把原来的教师都解聘了。张仰仁老师说,我们干不成,叫他们也干不成,雇了辆大棚车,把各班的优秀学生带上,到太原考学校。这样我就到了太原。
张仰仁老师有个朋友叫肖增绣,文水大象镇人,在太原山西省立商业专门学校当校长。张仰仁通过肖增绣的关系,把我们全部放到商专附设的中专乙种商业学校继续学习,他就回到陆军测量学校去了。商业学校是比较进步的学校,鼓吹新文化运动,大讲爱国主义,演出反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话剧。我还记得,演出《亡国恨》那个话剧的情况。戏里讲的是朝鲜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故事。据说这个剧本是农业专门学校的一个化学老师编写的。演出时,台上台下,慷慨激昂,掌声雷动,宣传效果极好。商校有个学生叫姚聪,安邑县人,在学校办了个“互助贩书社”,影响很大。当时,具有各种思想倾向的势力都比较活跃,新出的书刊也是多种多样,大多是以宣传为宗旨。给出版商写封信去,他就把书报刊物寄来,卖完再把钱寄去。这个书社给我提供了读书的方便,大开眼界。商校的另一个同学叫支应抡,号文才,晋南闻喜县人,和我特别好。他的大哥是反阎派,在陕西冯玉祥的部队里当军官。他介绍我结识了不少晋南反阎派人物。他还一手包办,把他的妹子嫁给我。后来,由于思想上的分岐,她一心要我在旧政权里谋个官做,我却立志要推翻旧社会。志不同道不合,终于又分离了。
就在我在商校读书的时候,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消息传来,我们都很激动,纷纷走上街头,游行、集会,向当局请愿,声援北京青年的爱国行动。伟大的“五.四”运动,是我走向社会斗争的第一步,它使我进一步认清了军阀政府的腐败无能,树立了改造社会的信念。
我在商校只住了一年。由于我不喜欢商业,第二年便考入省立门农业专门学校学农业。我在农校住了四年,一年预科,三年本科,于一九二三年毕业。在这里学到的关于农业的若干知识,对于以后我在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学工作,以及后来在家乡搞水利工作,都起了相应的作用。也就是在这期间,把我原来的名字张法古,改为张稼夫。所谓稼夫者,即“只问耕稼,不问收获”,到处散播革命种子的意思,很有点虚无飘渺、自由主义的气味。其实,在那时,改名换姓,也是青年们的一种进步表现,自以为挺革命,很时髦了一阵子呢。
我在农校学习的时期,结识了不少进步青年,其中,有当时一中的学生,后来成为山西早期地下党负责人的王振翼、贺昌、李毓棠、王瀛等人。王振翼和贺昌在太原办《平民周报》,宣传马克思主义,几乎每期我都我都看了。后来,他们组织“SY”小组,即社会主义青年团,我也参加了。我自己还办了个“真社”(真理之社),向教师募捐。收集各种报纸、杂志和书籍,供同学们阅读。我、贺昌、王振翼、王仿、姚聪、郭秀峰等人,又集资在开化寺办了个“晋华书社”,推销各种进步书籍。“书社”由姚聪担任董事,我是五元钱的一个股东。这一时期,我读了很多的书,进步的、落后的,革命的、反革命的,各种倾向的书都读。如: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人的经济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罗素的数理哲学,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印度的佛学,欧洲的无政府主义,以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等。马克思的著作也读了不少,如《价值、价格和利润》、 《剩余价值论》等。总之,接触的面很宽,感到都新鲜,都有道理。我好比在十字路口,反复比较,思想斗争很激烈,不知道哪一种理论能够救国救民。我和同学们争论,曾被人称为“新学博士”。我记得看过朱谦之的两本书,一本是《革命哲学》,一本是《现代思潮批判》。他什么都批,批马克思主义,批无政府主义,最后批他自己,什么都不要了。真是可笑得很。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马克思主义,有说服力,如“剩价值论”、“价值、价格和利润”的理论,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和压榨工人阶级的本质,分析的十分透彻。我在农校的第二学年,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也更多了。正因为如如此,也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常常受到申斥,罚我闭目静坐自省。我好动,坐不住就罚我面墙立正自省。然而,这一切,不仅不能使我屈服,反而更进一步加深了我对旧政权的厌恶,坚定了推翻旧制度的信念。
三
一九二三年暑假,我在农校毕业以后,就去了北京。
当时,凡是山西省立高等学校毕业的学生,毕业以后,还发给五十元银元到外地参观,回来以后必须到所谓“育才馆”,接受阎锡山那一套反动的培训,合格者才委以各种名目的工作,如县农桑局的实业技师,农事试验场的技术员,个别的还有委任为区长、县长的。实际上,当时许多先进学生都把“育才馆”称作“奴才馆”,不愿意去那里受训。我是学生会的主席,校里反阎派的主要人物,当然不愿意为阎锡山政府办事,领取了五十元光洋去了北京就不回来了了。
到了北京,我想继续求学。学什么,心中无数。不愿意学商业,也不愿意学农业。我在追求、探索救国救民,改变现状的真理。但是,我当时还没有能力去总结经验教训,指导下一步的努力方向。读书很多,可是杂乱无章,不知所从。已经二十岁了,仍在万状纷纭的意识形态领域,横冲直闯,徘徊彷徨,没有明确的世界观。一种苦闷的情绪萦绕在我的心头,常常是惶惶不可终日。那时,正是“五·四”运动以后不久,北京的各个大学都比较开明,只要不要文凭,哪一个大学都可以进去旁听,只要是穿长衫大褂,进出畅通无阻。我的盲目性很大,没有明确的学习目的。只要有可能,什么课我都去听。我本来学英语,听说蔡元培、马叙伦、鲁迅常去世界语专门学校上课,我也去学世界语。这时,我经济拮据,生活发生了困难。我想用半工半读的办法继续求学,曾计划成立个贩书社,一边卖书一边求学,未料到北京房租的押金太贵,碰了钉子。此路不通,于是另做打算。我又曾联合了几个人,想到内蒙去搞“新村。所谓“新村”,也就是空想的共产主义社会试验的一种不切实际的设想。当时,欧、美、日本都有办新村之说。但讨论来讨论去,不知该如何办,终于无结果而散。接着发生了曹锟贿选事件,我又参加了一个学生敢死队,反对贿选总统运动。不久爆发了直奉战争,冯玉祥倒戈,曹锟被打倒,宣统皇帝被逐出皇宫。戏剧一般地一幕接着一幕,北京城热闹得很。这时由冯玉祥率领的国民一军和胡景翼率领的国民二军进驻北京。胡景翼是老同盟会员,颇有胆识,他经过刘守中把我们那个学生敢死队改编为学生队,收编到第二军,列为营级编制。学生队的队长是陈春培,云南人。我被任命为上校政治教官并兼营军需职务。胡景翼收编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其目的是吸收新鲜血液,逐步改造他那支落后无知的旧军。所以我们这支学生队受到他特别的重视和信任。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孙中山先生到达北京,胡景翼就是派我们学生队给孙先生当卫队。受到孙先生的赞赏。
不久,国民二军调驻开封。胡景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王用宾为秘书长。他们为了扩大学生队,又招收了一些青年学生,把学生队分为两个队,一队队长是陈春培,二队队长就是刘天章同志。刘天章是陕西省人,北大的学生。此时,学生队干得有声有色,革命气氛非常浓厚。到开封后,国民军要扩充队伍,就派我到长沙招学兵。当时,毛主席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但是以赵恒惕为首的反动势力也很猖狂,斗争非常激烈。我拿着胡景翼写给赵恒惕的公函,带了两个人,一个叫田嘉禾,是湖南湘西人,一个叫薛同文,山西霍县人,到了长沙。赵恒惕的参谋长龚浩负责接待我们。我们在长沙登了招生广告,报名十分踊跃,一下子就招了好几百名青年学生。顺利完成了任务,胜利而归。这次和我们一同来长沙招兵的还有王英如。王英如字亦侠,山西临汾县人,太原女师毕业,曾担任临汾县女子高等小学校长。后来考入北京世界语学校。此人性情爽朗倔强,我和她就是在这个时候结婚的。我们从长沙招兵回来以后,大约在一九二五年的夏秋之交,军长胡景翼因臂上患疗疮突然死了,岳维峻接任二军军长,李纪才任开封警备司令。这些人行伍出身,丘八气昧颇重,见识风度远远不如胡景翼。他们看不惯学生队的革命作风,一上任就把我们的枪支给收缴了,学生队处于解散的状态。这对我的打击很大。巧得很,黄埔军校正招收第四期学员,我就把好多学生送去考黄埔军校。没想到却惹恼了队长陈春培,说我拆他的台,我们两人完全闹翻了。他给我开了个军用护照,撵我离开了部队。
我用仅有的一点积蓄买了车票,和王亦侠同志上了去北京的火车。那时,路途很不平静,王亦侠就女扮男装。当火车到达郑州时,扒手偷去了我们的钱和护照。不能往前走了,而而且,王亦侠同志女扮男装,又怕车警查出来,说不清楚,一路忐忑不安。过了彰德以后,我就向车长说了丢失钱和护照的情况,希望取得他的帮助。真是无巧不成书,坐在一旁的一个青年人听见我失窃,深表同情,并表示愿意帮助我们。经过介绍,知道他名雷鸣琴号五斋,陕西渭南人,是国民二军的军官家属,和他父亲一同去北京办事。他有一张护照,上边开了十几个人的名字,都没有来,又听说我是二军的军官,就让我和王亦侠用他的护照一齐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我们就去找高长虹。他是“狂飚社”的主将,山西省盂县人,是我在太原结识的朋友,常常在一块高谈阔论,关系很好,当时他住在北京沙滩的一个公寓里。通过郑效洵介绍我去北京汇文中学教书。由于生活所迫,我没有别的选择,便于一九二六年到了汇文中学,当了不到一年的教员。
一九二六年夏,在共产党的支持下,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北伐军节节胜利,短短三个月,就打到武汉,国民政府也随着迁到武汉,武汉成了全国革命中心。消息传来,我们心情非常激动。不久又听说,黄埔军校在武汉开办分校,并且招收女生队。王亦侠要去报考女生队,我也要去投奔北伐军,这样我们就毅然离开了北京。王亦侠同志于一九二六年冬、我于一九二七年初,先后到达武汉,开始了新的革命生活。
张稼夫 述
束为 黄征整理
(本站编辑:左丽)
主办: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晋ICP备15001143号-1
Copyright Shanxi Jinsui Culture Education &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9号院国投财富广场4号楼313/314 邮编:100073 电话:010-63395639/63395661 邮箱:sxjs9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