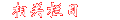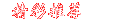
-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大力弘扬吕梁精神(06月21日)
- 悼念王军大哥(06月11日)
- “土窑泥坯”到军博(05月28日)
- 晋绥情怀和“智慧乡村”(05月23日)
- 2018年基金会工作回顾(二)(05月14日)
- 2018年基金会工作回顾(一)(05月09日)
- 贺大姐和红军后代到卢氏(05月08日)
- 军刀的故事(05月06日)
- 一位海军将军的期盼……(04月23日)
- 祭奠归来随想!(04月18日)
六十甲子经历(3)
发布日期:2017-04-28 12:07 来源:卢梦纪念文集 作者:卢梦
李延年 高沐鸿 鼓励写诗
那时正是1934年初,我回到太原后,就到教育学院学生宿舍找李延年。见面后一通名报姓,他表示知道我。我问他做些什么事,他说在养病,也写点稿子给“山西党讯”副刊发表,赚几个稿费。他说该副刊的两位编辑是教育学院的学生史纪言和王中青,大家都是熟人。随后他问我:听说你爱好文学,能写文章,是否写点什么给他们发表?我答应了。过了几天,我拿着我写的几首新诗给了他。隔了一天,就在“山西党讯”副刊上登载了。李延年对我说:编辑先生很喜欢你的诗,再写点吧!一来二往,后来也就认识了史、王二位编辑。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我写了不少短小的新诗和散文,在“山西党讯”副刊的“最后一页”上发表。那时,晚上常到副刊编辑部去送稿、闲谈,在那里还认识了常给副刊投稿的亚马、樊希骞等人。那时侯,我读的旧诗词不多,我写的新诗有的通俗易懂,有的难懂,内容大多是鼓吹革命的。

1984年12月山西太原“根据地文艺史料座谈会”合影(第二排左六为卢梦)。
有一次,我向李延年说我在太谷县参加过“社联”,回到太原后失掉了关系,问他是否能给我接转?他说他也没有联系了。后来我经过桑凯如的关系,认识了他的同乡、国民师范的学生阎建寅。我去阎建寅的宿舍次数多了,互相有了了解。他先是借了一些禁书给我看,如《马列主义中国革命观》及《血祭》等。后来我向他讲出在太谷县参加了“社联”,回来失掉了关系的事。过了几天,他帮我接上了这个关系。“社联”同我联系的人,后来知道他叫张国声。
有一天阎建寅给了我一个手抄本,说这是李延年写的一篇小说,让我读读看。小说约三、四万字,我一口气就看完了。这是篇报告文学作品,内容写的是清明时节,“我”(作者自己)与几个同志接受了油印党的宣传品的任务。但在城里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印,就假装去郊外春游,把油印机装在一个手提箱里;“我们”提着箱子出了城,到了双塔寺,登上了塔的最高层,有人“把风”,有人印刷,很快印完,带回了城里,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李延年在小说中描写一路上遇到的人和事及“我”的心情等等。这样的作品,用这样的形式在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中传阅,起了鼓励人们干革命、教育人们如何做秘密工作的作用。
哪个时候的国产电影,很多是表现青年男女谈恋爱的。对这种影片,李延年很反感。有一次他看了一部国产影片,叫《春水情波》,回来后很生气,说要批判,马上动笔写文章。写完交给“山西党讯”副刊,第二天就登出来了,题目是《春水情波、糖皮毒药》。
过了些时候,我去看他,屋子里没有别人,他说他有个计划,要翻印前些时候上海某个杂志上刊登的一个话剧剧本,叫《命令、撤退、第二道防线》。这个剧本我看过,是写1932年1月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日本军队的侵略,得到了上海人民的大力支援。战争正进行到紧要关头,突然接到国民党政府的命令,要他们撤退。接到这个不抵抗命令后,十九路军的将士们和上海人民非常气愤,但又不得不执行这个命令。这个剧本是揭露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的。李延年要把这个剧本铅印成单行本,在内部广为发送,以激起人们对国民党政府的仇恨。但他缺乏印刷经费,就准备向朋友们募捐,问我是否可以捐一点?我同意,凑了几元钱给他。单行本印出来后,他给了我几本,让我分发。
李延年大约是1934年冬去北京同仁医院治疗肺病的。在北京治疗期间,也并没有脱离开太原的革命文艺活动。1935年初,曾写了一篇较长的评论新诗的文章,寄来在“山西党讯”副刊上发表,鼓励了真正深入生活,写出了贫苦农民呼声的作品;批评了空喊口号、言之无物的作品。
李延年在“山西党讯”副刊上用不同的笔名发表过不少文章,多半是文艺评论,对于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理论,是有贡献的。虽然他没有写过长篇的论文。
在回忆当时太原的革命文学活动时,不能不提到进步文学活动的老一辈人物高沐鸿。
高沐鸿是山西武乡县人,1920年读初中时开始写诗,1924年参加了高长虹组织的“狂飙社”,写了不少诗和小说在刊物上发表,是山西老一代的新文学作家。他在家乡搞革命活动,受到国民党政府通缉,跑到了北京。1936年后半年,山西的政治形势好转,就由北京回到太原。他回来后,我和亚马等一些革命的青年文学工作者就经常去看他。他把这些青年当作小弟弟,亲热得很。我们常在他家里谈论一些文学创作上的问题。不久之后,他被当时的“太原日报”聘为副刊“开展”的编辑。这些青年文学工作者又有了个发表作品的园地。那时,太原市的文艺工作者们正酝酿成立全国文艺界抗敌后援会太原分会,高沐鸿在其中起了核心的作用。这是个松散的统一战线组织,有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参加,也有在政治观点和文艺观点上与他们不同的文艺工作者参加,前者做了些组织工作,后者大多只挂个名。这个组织成立后,出了个会刊,叫“笔阵”,就在“山西党讯”副刊上每周出一期,由我编辑。继这个组织成立后,山西省文艺界救国联合会也成立了。虽然救国联合会只是个空架子,不过我们可以利用它的名义,与太原的学生联合会、各界救国会等抗日群众团体联系,起了互相促进抗日工作的作用。哪个时候,虽然老作家高沐鸿自己创作的东西很少,但在有形与无形之中,成了太原革命文学活动的核心人物。
1934、1935年,太原革命文学活动的阵地主要是“山西党讯”副刊“最后一页”。
“山西党讯”是国民党山西党员通讯处办的一张小报,一、二、三版是新闻,第四版是副刊,刊登文艺稿件。为什么国民党办的报纸可以登载进步的文艺作品?这要从阎锡山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的矛盾说起:1932年南京政府领导的山西省党部成员开枪打死了一个请愿抗日的学生,引起了公愤。趁此机会,阎锡山赶走了国民党省党部的人。为了应付蒋介石,阎锡山就成立了山西国民党党员通讯处。这个通讯处只办了一张小报叫“山西党讯”,由一位山西省政府的中级官员主编。这个官员请当时在教育学院学习的史纪言和王中青编辑副刊,史、王二位编辑思想进步,就联系了一些思想进步的青年来投稿。当然,采用的稿子其内容是进步的,而调子是“低”的。以后史、王二人到长治师范教书去了,换了杨蕉圃当编辑。杨蕉圃一如既往,只要来稿不太露骨地宣传革命,不太“红”,就可以登。到了1935年秋后,阎锡山为了防御已到陕北的红军,对舆论工具加强了控制。“山西党讯”副刊的编辑换了人,不收外稿,只靠剪刀与浆糊来编。
1934年和1935这两年,我在这个副刊上发表过许多作品,用过十多个笔名,但经常用“卢梦”这个名字。这个名字的来源,是我写完第一篇稿子准备发表时,考虑要用什么名字?于是就翻开了字典,闭目用铅笔杆一指,第一次指到个“梦”字,又翻了一页,指到一个“卢”字,我把两次指到的字掉过来,就成了现在用的名字。用的次数多了,朋友们只知道我叫卢梦。但后来参加了牺盟会与决死队,就用我原来的名字:田振中。1940年到了晋西文联工作,又要写点文章,认识我的同志知道我叫过卢梦,于是又叫起这个名字来,一直叫了数十年,直到现在。原来的名字,几乎没有人知道了。
资料来源:《三晋文化研究丛书--卢梦纪念文集》 三晋文化研究会编
照片提供:卢梦之子田小明
本站编辑:林子
主办: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晋ICP备15001143号-1
Copyright Shanxi Jinsui Culture Education &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9号院国投财富广场4号楼313/314 邮编:100073 电话:010-63395639/63395661 邮箱:sxjs9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