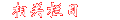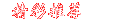
-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大力弘扬吕梁精神(06月21日)
- 悼念王军大哥(06月11日)
- “土窑泥坯”到军博(05月28日)
- 晋绥情怀和“智慧乡村”(05月23日)
- 2018年基金会工作回顾(二)(05月14日)
- 2018年基金会工作回顾(一)(05月09日)
- 贺大姐和红军后代到卢氏(05月08日)
- 军刀的故事(05月06日)
- 一位海军将军的期盼……(04月23日)
- 祭奠归来随想!(04月18日)
我的未尽之言--第一章(一、二、三)
发布日期:2016-02-19 16:18 来源:未知 作者:晋绥基金会
第一章 太原三年牢狱生活
一、在太原参加革命斗争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国民党政府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掀起汹涌澎湃的爱国救亡运动高潮。热血青年学生冲向前列。正在山西太原成成中学读初中的我,在这国家危亡、民族觉醒的关键时刻,再不能忍受旧观念的束缚,勇敢地投入爱国学生运动的战斗行列。参加了太原市“一二·一八”的抗日反蒋救亡运动,声援“一二·八”淞沪抗战。在火热的学生运动中,我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有了初步觉醒。
我是1930年夏天考入成成中学的。我原籍本在福建,1914年5月生于福州市。出生前后父亲在荷属东印度的爪哇(今属印度尼西亚)教书,收入微薄,无力抚养子女。我刚出生不久,就被送往连江县外祖父家寄养。外祖父是清末举人,在连江一带颇有声望。13岁以前,我在外祖父家读私塾和小学。14岁父亲任职于盐务稽查局,被派到山西工作,跟随父亲到了山西忻州(忻县),在那里读完高小,17岁又随父亲迁居太原。成成中学是北平师范大学晋籍毕业生于1924年创办的一所私立中学。第一任校长肖静庵鼓吹“苦读救国”,反对学生接触革命思想,限制学生参加政治活动。肖某热衷名利,经常奔走于军政要员之间,在他看来办学只不过是谋取高官厚禄的手段。1932 年初,肖被山西当局调往太原进山中学任校长后,成成中学校董事会推举共产党员武新宇接任校长。共产党员刘墉如任训育主任,另一位共产党员刘丹敦不久也来校担任了教务主任,该校教师中也有一批共产党员,成中一跃而成为一座充满革命活力的学校。1933年1月,阎锡山查封了“抗日反帝大同盟”,逮捕了其领导成员及骨干分子。武新字、刘丹敦是这个组织的主要组织考,被迫离校出走。山西当局乘机派回曾任该校训育主任、早已调离的段炎离出任校长。段某是阎锡山反革命组织“中国青年救国团”骨干分子,一进校门就说:“我是带着宝剑来的!”随即辞退革命教师,解散学生社团,禁止进步活动。中共山西特委为了夺回成中领导权,于5月间发动学生罢课,展开“驱段斗争”,段炎离在校横行三、四个月就被赶走了。
我在成成中学读完初中,1933 年夏又考入高中,一直读到1934 年春。在武新宇、刘墉如、杜心源、张衡宇、刘丹敦、焦筱宗(焦国鼐)、张丽云等进步老师们的指引和启蒙下,我热切地阅读了一些社会科学和马列主义的书籍,深受新文化思潮的熏陶。曾经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们倡导组织读书会、办墙报等活动,关心时事,交换心得,研讨学术。特别对我们有影响的是华岗所著的《中国大革命史》。我们参加“社联”时组织上出题考试,出的题都在华岗这本书里,所以我们答得都很正确。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国民党政府步步退让,我深感国家危亡,匹夫有责,激起救亡图存的意念和追求 ;进步的强烈愿望。对曾窃取成中校长的肖静庵、段炎离之流的反动统治,感到极度不满,不堪忍受,便与不满现状的同学一起,团结全校同学展开斗争。经过斗争的实践,自己在思想上初步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如前所述,成中在三十年代发生两次夺取学校领导权的斗争。第一次是广大学生不满肖静庵、高阆仙的旧办学观点,学生们严厉地给予批判,并热烈拥护武新宇当校长。经过斗争,校董会批准了武新宇当校长。第二次是同学们起来和拥护段炎离的人作斗争,终于撵走了“中国青年救国团”骨干段炎离,拥护刘墉如为校长。在校董会推选和群情激愤下,教育厅不得不批准刘墉如当校长。成中领导权,又一次掌握在共产党人和进步教师手中,在成中两次夺取学校领导权的运动中,使我深深认识到在白色恐怖下,领导权掌握在谁手中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成中能否夺取并巩固领导权,实质上就是能否在成中保留革命火种,坚持革命阵地的首要问题。事实证明,只有接受成中在白色恐怖下屡遭破坏和损失的教训,认真分析在反动派控制下的复杂局面,总结出对付敌人的一套策略手段和方针方法,耐心做好思想教育的艰苦工作,才能夺取斗争的胜利。经过这些斗争,使我得到了实际的锻炼和提高。
成中在三十年代中,在进步老师的辛勤哺育下,终于开花结果,卓有成效地培养了不少革命力量,成为党在各方面的中坚骨干。特别是抗战开始,刘墉如老师呕心沥血地建立了一支近400名的师生游击队,开赴前线,浴血奋战。有百余名师生,将自己的头颅和鲜血抛洒在大青山的疆场上,表现出铮铮的骨气、耿耿的丹心。为成成中学,在中国现代史上写下了光芒四射的光辉篇章。在我回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怀念!1986年在太原召开晋绥党史座谈会期间,我跟随着成中的老师和同学,一致向山西省委倡议;将现莅的太原市第三中学,恢复成成中学的原校名,以传颂后人,永志不忘。
1933年秋,由张积玉(张永青)同学介绍我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社联”,在成中同时参加的有阎伟(阎秀峰)、龚允恭、张积玉和我共四人,组成成中“社联”支部,张积玉任支部书记。寒假张积玉回家,我代理支部书记。同时太原“社联”调我为太原市“社联”执委会委员。1934年初,我参加了共青团。从此奠定了我革命的基础,树立起共产主义的信仰,开始了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革命生涯。由于当时思想幼稚缺乏经验,于1934 年“五一”前夕被捕。同时被捕的有阎伟、龚允恭、王伦等四人。我们四人被捕,使成中“社联”支部遭到破坏,虽然这是一次失败,但在政治思想上,却换来了难得的锻炼。
二、被捕经过和公安总局审讯
1934年初,我参加太原市“社联”执委会。“社联”执委指承,要建立一个机关,主要印刷“社联”的秘密刊物和传单。指定由我们成中“社联”盟员负责筹办。不久即在离我们学校不远的小北门街31号的一个大杂院,租了后院一套里外间的房子。住机关的有阎伟、张积玉、龚允恭和我共四人,还有一名工友全喜帮我们做饭看门,一切费用由我们几人节衣缩食来负担。我们负责编印太原“社联”执委会刊物《红旗》,《前夜》墙报改为油印刊物,也在这里发行,并联络其它几个学校,及时传送“社联”文件。在派出所登记的户口是以成中学生宿舍为名,对外说法是为迎接全省会考复习功课。这时我们四人已不再到校上课,完全脱离学校生活。在这里同住的除我们四人外,“社联”上级还派共产党员梁膺庸来指导我们的学习和帮助我们的工作。梁当时报户口,用的是陈君的名字。
1934年4月30日“社联”执委指示,要成中“社联”;”盟员,于当晚到街上散发、张贴纪念“红五一”、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对法西斯会考,宣传抗日等内容的传单,或书写粉笔标语。我们成中“社联”盟员分四路出发。龚允恭和李如桐一路,阎伟带王伦一路,张积玉独自一路,我的任务是到各学校传达“社联”指示,并送发《红旗》刊物和《穷人报》等宣传品。
阎伟和王伦到公安局附近散发传单并写粉笔标语。王伦被警察抓捕,阎伟逃脱。王伦年龄小,刚入“社联”不久,受刑不过,供出我们的住处和“社联”盟员。阎伟逃脱追捕,回到住处,告知王伦被捕情况,与已回到住处的张积玉、龚允恭研究如何办。决定张积玉先去成中报告王伦被捕消息;阎伟、龚允恭两人留在住所。时间过久,他们等我不及,写了“我们走了”的纸条,压在桌上的煤油灯下,提醒我的注意,就匆匆离开住所。迟至夜12时以后我才回到住所,极度疲乏,和衣倒下就睡,根本未注意灯下压的纸条。睡梦中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警察已破门而人,即被押走。警察把房间所有的东西洗劫一空。我被抓走后,阎伟和龚允恭为探听我的下落,天刚亮又返回住所,被埋伏在周围的便衣警察逮捕。我们就这样先后在1934 年“五一”前夕被捕。
“五一”清晨,我被拘留在公安分局。不久,就看到阎伟、龚允恭两人也被捆绑押来,心中十分沮丧。在警察的严密监视下,三人同在公安分局拘留一夜。第二天,公安分局转押我们去公安总局的途中,趁警察们疏忽的间隙,我们机智地串通口供。我告诉龚允恭、阎伟说,和我被捕同时,有一箱子“社联”文件被抄走,能推脱就推脱。如推脱不了,则只能分别承认是“社联”一般盟员,更要强调“社联”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学术团体,不涉及任何政治。对担任“社联”领导职务和“社联”秘密机关,共青团员身份,特别是对陈君同志坚决不能暴露。对张积玉的去向,特别是陈君其人,要矢口否认。决不许有丝毫暴露。必须坚持革命气节,不畏严刑拷打。我们三人被押上囚车,解送到公安总局,分别被投入到十分恶劣的拘留所监房内。拘留所监房是个三、四平方米的小间,污浊不堪,臭气熏天。睡在腐烂破裂地板上,老鼠满地窜来窜去,竟咬破了我的脚跟。每餐一碗小米饭、一片咸菜、一支筷子(是反动派污辱犯人的做法)。同住的有两名普通犯,其中一名老者,看到我年幼体弱,在我受刑后表示同情。不几天,我被押到公安总局三科,由特务潘建如审问,此人心毒手狠,极其残酷。
在三科审讯时,他们狡诈地让王伦出面对质。王伦指着被叟查出有阎伟、龚允恭、张积玉的像片说,像片上的人都参加了“社联”组织。法庭上还出示被抄来的所有东西,箱子内的《红旗》刊物和印刷用具等,特别有我写的一份自传材料,其中提到我和张积玉、词—伟、龚允恭参加“社联”的字样。有了人证、物证,我就难以辩驳,参加“社联”即被他,他们定案。在以后审讯中,潘建如肯定地说,“社联”就是共产党,你就是共产党。我辩解说,我不是共产党,“社联”也不是共产党,“社联”和孙中山 先生遗嘱“……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宗旨是相符合的。这一辩解,激怒了潘建如,他气急败坏地猛拍桌子,嘶嚷着要动刑。两个警察一左一右接着狠命地打我嘴巴,待下堂时,满口鲜血直流。以后多次审讯,都是追问陈君何许人,以及去向下落。“社联”领导人李延年曾告诉我,陈君是共产党员,要我们尽力保护,这一点我牢记不忘。审讯堂上,不管他们如何恫吓威胁,或是转弯抹角地审问,我就是一个老主意,只说陈君是我的朋友。但对陈君的形象,我们四个人各说不一,更加引起他们的怀疑,加紧逼问。因得不到证实,屡令施刑。警察用竹板毒打两三次手板,两手冒起很高的血泡,两臂全然失去知觉。还施行坐老虎凳的刑罚,垫了四块砖我即昏去。当时,我患严重的“血伤寒病”,鼻孔流血不止,四肢无力,身体极度瘦弱,由于前几次的审讯,都未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他们看到我重病在身,穷追不舍,想趁机逼供。对我还要用踩杆子的特重刑具来诈呼。但我没有被他们所吓倒,就是闭口不答。我虽吃尽了苦头,敌人的阴谋却破产了,他们没有得到任何东西。直到5月底,我的病情稍有好转,公安局将我们四人一同转押到高等法院审判,关押在太原地方法院看守所里。当时我是20岁。
三、在地方法院看守所的十八个月
1934年5月底或6月初,阎伟、龚允恭、王伦和我,从公安总局被押到高等法院,关押在地方法院看守所。直到1935年底,大约有十八个月。
那是一个昏暗的夜晚,拘留所的警察们将我们四人提出揪到囚车上。我们怀着不安的心情,不知这些反动派将如何地处置我们。拘留所那位同监房的老者,曾向我讲过,如果送你去法院,问题就好办些,我唯愿如此。天大黑时,果然是押进地方法院看守所。而且我们四人被关在同一监房里。这个监房门的上方,有一方形的窟窿供看守人员监视犯人之用,门的下方还有一个小洞,供晚间小便之用。
我们被关进看守所,天色已晚,想不到半年前被捕的成中老师张衡宇还关在这里,前来看我们(据说凡系社会上有身份的人所住的监房,晚间不上锁,可自由出入)。我们四人兴奋地轮流在门口上和他交谈。张衡宇老师先问我们被捕经过。我们简要地向他做了汇报。张衡宇老师对我们年轻人勇敢而又幼稚的表现,极为赞扬,开怀地大笑起来。同时也简单地向我们介绍看守所关押的政治犯和看守所内部管理及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就这样,我们伸着脖子在窟窿上和他足足谈了两个多小时。夜已经很深了,大家仍是依依不舍。这晚我们四人挤在一个炕上,心情十分愉快,原来的忧虑不安一扫而光。
二天清早,警察打开监房的门锁,所有被关押的政治犯部到院子里放风。这是两个长方形的小院,每院有七、八间监房。中间有木栅栏相隔,看守们在木栅栏内来回走动监视。院内关押有20名政治犯,其余皆是普通犯,不久普通犯调离别处。我们一露面,大家蜂拥而来,问长问短,特别关心外面的情况,又问及我们四人的情况。你一言,我一语,简直使我们接应不暇,大家极为热情。有的送自己仅有的一点食物;有的招呼打水盛饭。普通犯们也都围过来,亲热地啦啦呱呱,都感到无比热切和温暖。我们虽是被关押的罪犯,但在这个小天地内还是有一定的自由。
看守所是关押等候审判的犯人。我们四人经过公安总局多次审讯,到这里等待判决。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只提审过几次,提问的仍是公安总局的那些问题,我仍然坚持过去的供词,丝毫未加更改。在以后长时间内就是等待判决。所以这期间我们可以利用的时间很多。
这里的政治犯中,有革命的长辈,也有同辈的革命青年,和我们日夜相处,使我得益颇多。所以我把它看作是我的第一所受革命教育的学校。张衡宇老师有白区工作经验,对革命工作稳妥求实,对同志赤诚相待。在成中任教时,他热情启发和指引青年学生走向革命道路,并耐心地培养教育。被捕后,他仍具有这种精神。他和外面党组织保持着联系,建立起看守所党支部。他在牢房里,积极努力工作,对政治犯热情帮助,关怀备至。他还非常巧妙地做看守的争取工作,使看守们能帮助我们做事。给我们送来很多报纸和书籍,保证了精神食粮的供应。为此,有人告发张衡宇老师,他曾受过法院的审问。他孜孜好学,在看守所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他始终坚持不懈地学习日文。他积极组织大家有计划地进行学习,倡导青年们学习马,列、学外语。当时在政治犯中学习空气浓厚,有学日文的,有学世界语的,有学新文字的,我学的是新文字。张衡宇老师出狱后,抗战初期,在晋西南六专署工作,晋西事变后调北方局。1941年我去北方局汇报工作时,正值他下乡不在机关,他写给我一封热情洋溢的长信,回忆狱中生活和他在工作岗位上的某些体会,使我倍感亲切。就在第二年6月7日,在日军大扫荡中,张衡宇老师因背上受重伤的同志不幸陷入日寇包围,他从容地拔枪射击,接连打死两名敌人,在和敌人搏斗中壮烈牺牲。他的英勇牺牲和他对我谆谆教诲的形象,使我深深地缅怀。当年在看守所的政治犯中,还有老党员阎瑞生生(阎子祥),沉着坚定,富有基层工作经验。白丙喜(白玉生),有丰富的的白区工作经验,坚贞不屈,曾多次住过监。病号监的王孝慈,有水平、有能力。我们青年都尊敬他们为老师。病号监和王孝慈同居一室的郭万富(现名郭万夫)、马希贤是和我们四人一样大小的青年人,受到王孝慈很多教育和培养,他们虽然没和我们编到一个小组,但和我们关系密切,经常来到我们房间谈些问题,交流学习心得。其他如张建古(后名张德含)和稍后来的李楷(李逸三)、李文俊、郭钦安、李友杜(李远)他们都是共产党员,都有工作经验,是我们的亲密战友。马延龄、胡祥(工人)、李公选(李唯一)这些人都是好同志,我和他们接触不多。王光甫(叛徒)、姚玉祥据说被捕后表现不好。朴解生(朝鲜人)是医生,当时他积极为我们看病。
我们关在地方法院看守所,开始一段时间,张衡宇老师集中了解我们成中和太原市“社联”的情况,并考察我们每个人被捕的具体细节,以及我们每个人在审讯中的表现。他说,我们在敌人法庭上坚持革命气节是很好的,缺点主要是在学生运动中和“社联”工作中有某些左倾幼稚病的表现。不久,张衡宇老师向我宣布:组织上决定恢复我的共青团团籍,并指定我作发展阎伟加入共青团员的介绍人。我们在狱内苦斗中,收到了互济会转来的、过去与我们参加抗日反蒋学生运动的亲密战友、成中第一任“社联”支部书记张积玉的来信,给予我们很大的鼓舞和安慰。这次写回忆录时,可惜我记不起张积玉来信的具体内容。当将回忆录寄送张积玉同志征求意见稿时,感谢张积玉承他帮助回忆。现将其回忆补写如下:你被捕后,我参加了赤色互济会,冬天回到太原。得知你们在狱中表现很好,吃了好多苦头,英勇斗争,并和外边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我还给你们写了一首歪诗,托互济会转去,鼓舞你们的斗志。当时外边的党组织,对于被捕的同志是很关怀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如果你们有什么说道(意即表现不好),一定会通知有关的人小心。对于表现好的同志,也要告有关的人给以鼓励和帮助。我当时是没有收入的,所以只有用诗来表达我的敬意与情谊。现回忆诗的大意是:
亲爱的朋友们,我关心着你们,
因为你们正直,
正直的人,总是要受到诬陷的,
邪恶是正直的对立面,它伴随正直而来,
这就是规律、规律、规律……
可别忘记规律的另一面
——“邪”不压“正”。
最终“正”是要胜利的。
现在是曙光将要出现的时候,
天突然变得寒冷了,
阴沉沉地什么也看不见……
等待吧!
曙光就要出现。
你们的生活怎样呢?
有病吗?身体还好?有书读吗?
我们是读书人呀!
张衡宇老师组织我们学习。我们四人编为一个小组,规定先学两本书:李达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列宁著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内容深奥,极其难啃,幸有张衡宇老师的辅导,才略有粗浅理解。我们受益较多的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本书里的一些原理。根据这些原理,检查在学生运动和“社联”活动中,犯有不实事求是,脱离现实的左倾幼稚病的错误,太原“社联”一再指示要我们大力开展工人和农民工作。我们曾到铁路找工人谈话,过汾河访问农民。我们根本不熟悉工人、农民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他们看我们是学校里的学生娃娃,互不了解,而且调查、访问时间有限,聊点日常生活还可以,推心置腹地交谈,根本办不到,更不用说互相交朋友了。实际上到工厂去调查是走马观花,到农村访问是旅游式的转圈圈,结果是毫无所得。为“社联”所写的指示和文章,多是高谈阔论的空喊革命口号。实际上,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在我们力量很薄弱的情况下,都是办不到的事情。因此,只有每天晚上,到街上写些标语,散发传单。太原“社联”执委会,调人到上级机关工作是需要的,但不需要那么多人都到执委会机关工作,按工作量有一两个人就够了,放弃成中这块革命阵地是很不对的,多数人应该留在学校工作。在成中多年的工作比比较熟悉,而且也有做学生工作的经验。同时成中当时处在白色恐怖中也有困难,成中“社联”还需要大大发展,壮大力量。因此,需要我们支持成中的工作,把骨干都调走,对成中是有损失的。造成我们被捕和“社联”被破坏的教训是深刻的。经验证明: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必须严格分开。我们几个既不完全脱离学校,又不到校上课,是成中的挂名学生。建立秘密机关报户口是成中学生宿舍,从没有想过这里一旦发生问题,就会危及学校。这种情况都是违反秘密工作的原则的。纪念“红五一”出发前,对秘密文件和印刷用具,原封末动,未加任何地清理和转移,也没有订立联系的警号和暗号。那天我深夜返回,即使看到灯下的纸条,也难以判断发生了什么问题。王伦被捕,阎伟、龚允恭不听张积玉同志的劝告,不从工作着想,完全是感情用事,返回住所,结果是自投罗网。“社联”秘密机关宿舍墙上悬挂着阎伟、龚允恭、张积玉的像片,也是秘密工作不许可的。太原“社联”执委会,派来陈君帮助我们学习工作,我们没有订立下一套合乎情理的明确关系,不合秘密工作原则。我们检讨出的上述粗浅经验,都向白丙喜、阎子祥、张衡宇请教改过。经过这段学习和请教前辈同志,反省过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题,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进行革命斗争,不仅仅是要有足够的不怕死的勇气,更重要的是须有和敌人作斗争足智多谋的策略手段和应遵守的革命纪律。
我们在看守所和阶级敌人进行过三次面对面的斗争。
一是与叛徒作斗争。叛徒王光甫和我们同关在一所监房内,王光甫平时表现出随随便便、满不在乎的样子。看守所的老同志,对其出卖地下党秘密机关山西特委秘书处,使张衡宇、阎子祥等一大批人被捕,机关遭受破坏非常气愤。大家议论起来,特别看到他那毫无悔改的样子,气愤不过,要揪出这个叛徒,教训教训他。王光甫开始还气势汹汹,企图辩解,更激起大家的愤怒。张衡宇老师劝阻大家不要动手,但要充分揭露他出卖组织和自己同志的罪恶,指责他在敌人面前屈辱投降,不惜出卖党的组织、出卖同志,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是一名可耻的叛徒。大家对其丑恶嘴脸嗤之以鼻,反动当局怕他再遭受政治犯们的围攻,将他调往别处。这一番斗争,是一堂具体而又生动的气节教育课。王伦和我同住一监房。这天晚间,王伦流着泪向我表示,说他和王光甫一样是出卖同志和组织的叛徒,懊悔不已。我诚恳地指出,你是有错误的,但重要的是你个人已经认识自己的罪过,愿意改悔,并在行动上有所表现,与那些恬不知耻、死不悔改的叛徒是有区别的。王伦一再检讨,并决心改正错误,从新作人。
二是围攻来狱中“视察”的司法部长王用宾。大约在1935年春季,有一天忽然看守所所长、十长①及看守们,拥着一个昂首阔步、官气十足的官老爷来到监房。看守所长在前开路旨手划脚地要我们政治犯全体出来,毕恭毕敬地介绍说,这位是司法部长王用宾,前来看守所视察。这位傲慢的官老爷,慢条斯理地似乎要开口训话。这突如其来的场面,使我不知所措,难道甘愿听他训话不成!正在这个严重时刻,张衡宇老师、白丙喜、张建古三人机智地从我们行列中跨前一步,严肃地向这位官老爷提出质问:看守所为什么不把政治犯当人看待,限制探视,不照料病号,没有卫生设施,不许看报纸。继而揭发看守所长克扣囚粮,监房尽吃霉粮,饭不足量,每餐只一片咸莱等情况。他们三人态度沉着,据理以争,口若悬河,侃侃而谈。使得看守所长惊慌不安。这位威风凛凛的王用宾,无言对答,只好尴尬而去。他们三人在统治者面前,这种不失时机的大义凛然、能言善辩的才能,令我衷心地钦佩。认为这也是作为一个革命者,必须具备的灵活机智和善于言词的能力。从此我们学习小组规定,每当同志们在小组会上发言都要站起来,严肃认真,以锻炼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应有的气魄。回想起来,这虽然是幼稚可笑的,但也反映出青年人好学的表现。
三是为改善政治犯的待遇而进行的绝食斗争。我们向王用宾所提问题和要求,看守所一直置之不理,毫无解决之意。大家即决定发动绝食斗争。这次绝食斗争,事先做了周密计划,成立绝食斗争委员会,由张衡字、白丙喜和我(我是代表青年的)三人组成。委员会主要掌握绝食斗争的组织和策略。为了照顾病号和体弱者,决定朴解生不参加绝食,以便照料绝食同志,在绝食进行中负责给大家送水,暗中加少许盐和糖,以维持体力不致受到太大的损失。我现在只记得提出的条件有这么六条:不吃霉小米吃好小米;生一炉火供大家使用;订一份报纸;取消夜间上锁规定;要求洗澡;能与来探视的人当面交谈。绝食坚持六天六夜,年长者显然虚弱,难以坚持,我们青年人仍生气勃勃。统治当局陷于被动,看守所长亲自出面,劝说复食。张衡宇、白丙喜等强硬拒绝,一再表示,不答复要求,绝不复食,并拿出一篇稿件,要求登报,由社会公论。看守所深怕事态扩大,对自己不利,答应了所提全部要求,由看守所长签名盖章。我们绝食斗争胜利了。宣告复食的那天,当局担来两桶鸡蛋挂面条,长者们劝我们小青年,不能一次吃饱,否则会损伤胃肠的。自此斗争以后,一段时间内,我们能吃到新鲜小米,每餐有稀饭,多加一块咸菜。院内设立炉灶供大家使用,传阅一份报纸。洗澡间虽修理过几次,始终来能使用,允许轮流到病号监的的澡堂洗澡。
有了炉灶,大家商量改善生活。外面有亲友送来食物,大家共同吃,收拾炉灶、和煤砖、掏炉灰、做饭、洗碗等活计,大家主动干,形成一个欢乐的集体生活。我父亲每周为我兄弟俩送来一袋面粉和一篮子肉菜等,张衡宇、阎伟等外面都有亲友,不时送来食物,大家一齐动手做饭,共同享受。同时还想出许多办法,用监房的玉米面窝窝头,揉碎与白面掺半做成两和面的馒头,既省面粉,味道又好。
这一年5月间,我们纪念马克思生日,同时庆祝绝食斗争胜利。借口要晒被褥,在院内幕布式地一层一层挂起来,在好看守值班时,我们大家钻到被褥后面开起会来。会上谁讲话谁发言,内容是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我被幽禁在地方法院看守所共计十八个月的时间。绎讨几次审判,最后判决我三年徒刑。此时是1936年2月,当时我是22岁。
注
①“十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山西阎锡山的监狱中一种看守人员的职称。—编者注
本文摘自:龚子荣著《我的未尽之言》
本站编辑 左丽
主办: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晋ICP备15001143号-1
Copyright Shanxi Jinsui Culture Education &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9号院国投财富广场4号楼313/314 邮编:100073 电话:010-63395639/63395661 邮箱:sxjs9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