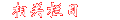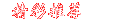
-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大力弘扬吕梁精神(06月21日)
- 悼念王军大哥(06月11日)
- “土窑泥坯”到军博(05月28日)
- 晋绥情怀和“智慧乡村”(05月23日)
- 2018年基金会工作回顾(二)(05月14日)
- 2018年基金会工作回顾(一)(05月09日)
- 贺大姐和红军后代到卢氏(05月08日)
- 军刀的故事(05月06日)
- 一位海军将军的期盼……(04月23日)
- 祭奠归来随想!(04月18日)
我的未尽之言--自序
发布日期:2016-02-19 15:19 来源:《我的未尽之言》 作者:晋绥基金会
龚子荣
在漫长的革命工作中,特别是在执行党的路线、政策时,难免会遇到某些思想上想不通的问题。这就要求能切实地学习和领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学习党的各项政策,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解剖自己,分析客观事物,从而总结出有益的经验教训,判断历史的正误。这个小册子收入的几篇回忆录,都是本着这个原则撰写的。这几篇回忆录或曾刊登在内部刊物上征询各方意见;或邀请有关同志座谈听取过他们的意见,再修改、再补充而写成的。
下面再谈谈一些意见:
《太原三年牢狱生活》主要叙述我三十年代被捕和狱中生活的详细过程。为什么我要写这篇回忆录呢?1980年间我抱着困惑和怀疑的心情参加广东省讨论起草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到中央正式公布该决议时,我又看到邓小平同志对起草这个决议的意见。决议中尖锐深刻而又实事求是地批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认为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并正确估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确立毛泽东思想。经过深入学习,反复思考,使我消除了一切困惑和怀疑,心悦诚服地接受决议的观点。及至东欧剧变苏联遭到解体的悲惨结局。我更深一步地理解六中全会决议的远见卓识。我更信服地认为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只能以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为准则。
回顾文化大革命运动,一些帮派利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做了许多坏事,使一些老干部遭受迫害。当时中办负责人领导的中央专案组第一办公室(简称“一办”)和中央办公厅专案组,借审查干部为名,私立公堂,妄加罪名,陷害老干部。典型者如他们罗织杨尚昆同志的所谓窃听窃密案件,纯属弥天大谎。当时中办负责人对个中真情原本是完全了解的,却任其编造牵连很多人。我被株连为“杨家死党”之内,更被毫无根据地打成叛徒。尤其无法理解和不可容忍的是,早在1967年底或1968年初,建筑工程部专案人员到南京敌伪档案查阅阎子祥的材料,顺便查到了有关龚子荣的材料。材料证实1936年 11月20日山西高等法院首席检查官田汝翼致司法部长函称:“兹查龚允济(即龚子荣)一名,自到反省院以来,屡与其他反省人员秘密接谈,从事鼓动,一再训戒,毫无悔改。”为此加判五年徒刑,送山西第一监狱执行。建筑工程部将此材料送“一办”和中办专案人员。他们无视这一重要旁证材料和郝一民等几位同志有价值的证明,并将其搁置隐匿起来。反而向总理汇报说在五大区十来个省市查阅上万卷敌伪档案,找了近百名旁证人,揪出了隐藏三十多年的“叛徒”龚子荣;另一方面对我多次申诉不加理睬,长拖不决达十二年之久。1976 年竟然不顾事实,正式做出定我为“叛徒”,开除党籍,保留公民籍,每月发150元生活费的处理,要我签字,遭到拒绝。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虽给我做出平反昭雪的结论,但在结论中还想托辞掩盖其错误。至今我未听说中办专案和当时中办负责人对如此骇人听闻的冤案,有什么自责和检讨。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写这篇《太原三年牢狱生活》回忆录,送中央存档备查。此文是在送请三十年代与我同坐牢的同志们的审查、核实修改;改之后定稿的。
这本小册子中收入了《晋绥土改整党的回忆》一文。我为什么要写这篇回忆录呢?1949年全国解放后,广大新区进行土改是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极大解放生产力的伟大运动。我认为新区土改的胜利完成,是党中央、毛主席深刻吸取了1947年在老区、半老区土改整党工作中走过的弯路和所犯的错误,总结出经验教训,从而制定出更切合实际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当时党中央、毛主席发布了与土改直接、间接有关的指示有百余篇之多。其中最著名的有《中央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和任弼时同志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和《对晋绥土改整党工作的意见》的两个电报。由此可见虽然1947年老区、半老区土改中犯了猎误,工作上受到暂时损失的坏事,经过党中央的纠正和总结,又变成了好事。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这就是我为什么特别重视1947 年晋绥土改整党工作中的问题和所犯错误,并寻求其经验教训,写成回忆录,听取各方意见数易其稿的目的所在。
我在这篇回忆录中,所讲晋绥分局主要领导同志是指李井泉同志。首先我要说明,李井泉同志是位好同志。他有许多优点值得我学习。他过去任晋绥分局第一书记时,我很尊敬他,直到他逝世后,我仍然是抱着尊敬的心情怀念他。李井泉同志当时对中央关于晋绥分局土改整党工作的批评一般说来是尊重的,并于1948年制定了对土改整党的七个《纠偏文件》。1948 年底召开的晋绥边区党代表会议,他没有到会,贺龙同志自始至终参加会议,发扬民主,与会者对土改整党谈了许多批评意见,最后由分局副书记张子意同志做了总结。尽管总结的检查不够彻底,还有许多值得研究讨论的地方,即便如此,也得人心。在1948年后的四、五年间,对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和恢复生产力,都起到了很大作用。我认为李井泉同志在1947年土改整党中所犯错误是思想认识上的错误,而其错误:没有得到纠正,在以后工作中继续存在,其根本原因是李井泉同志骄傲自满、独断专行,不能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在工作中一直不能接受自下而上的监督批评,因此停不到、听不得不同意见,而逐步形成的。
关于晋西南革命根据地问题也要说几句话。在晋绥革命根据地史料征编工作过程中,有种意见认为:“1940 年以前晋西南、晋西北两块抗日根据地党的组织同属于北方局领导,相互问并无直接联系。晋西南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115师在抗战初期创建的,而晋绥抗日根据地(包括晋西北地区和绥蒙地区)是八路军120师创建的。所以1939 年前晋绥抗日根据地不应包括晋西南抗日根据地。两个抗日根据地的史料应分区单独进行征集”。还认为“晋西事变后,在晋西南地区虽然仍有我党秘密活动,仍有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但编写党史、军史、革命斗争史与编写抗日根据地史应有所不同。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它游击部队,在日寇占领的后方,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政权,保存和发展抗日力量,消灭和驱逐侵略者的战略基地。晋西事变后,晋西南地区于1940年4月即划为阎锡山的管辖区域,我党中央也明确指示‘分疆而治’。所以,晋西南不应再算作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应该称‘特殊的抗日统一战线地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其用意明显地是在编写晋绥革命根据地历史中要撇开晋西南,晋西南地区应另行编写其历史。
为什么说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呢?晋西南抗日根据地是是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创建的。早在1937年9月20日,毛泽东主席致八路军将领的电报指示:“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在山西应分为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敌人,取四面包围袭击之姿势,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是难以立足的。”10月下旬,日军沿正太线猛烈进攻,毛泽东又一再明确指出:“吕梁山脉之晋西南,虽然目前距敌尚远,然亦不可不于此时作适当之部署。”八路军第115师主力和表面上属晋绥军建制,实际上由中国共产党所组织、领导的山西新军,在日军侵占占之前数月就已进入这个地区。在晋西事变以前,它同晋察冀、晋冀鲁豫与1940 年以后的晋绥边区这些我们力量占绝对优势的根据地比起来,确有自己的特殊性。它是一个特殊的统战地区。在这里,进步力量和反动势力交错共处,阎锡山的总部也在这个地区。两种势力同时并存,从创建开始就充满矛盾和斗争。但它不仅是按照中共中央部署创建起来的,而且在这里普遍地建立发展了党的组织、人民武装、群众救国团体和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在实际工作中都认真地贯彻执行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及党所制定的各项抗日政策。在这些最主要的方面,它同党所领导的其它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本质上并无区别。而晋西北地区在晋西事变之前的情形也是这样。晋西事变后,整个晋西南、八路军主力部队和新军统统撤到晋西北,把晋西北旧军赶走,共同建设新的晋绥革命根据地。党的领导机关是晋西北、晋西南合并而成。以晋西南区党委书记林枫为书记、晋西北区党委书记赵林为副书记,建成晋西区党委,以后改称为中共晋绥分局。从此晋西北和晋西南合为一体。至于晋西事变后,晋西南党处于秘密状态,当 然不能称为革命根据地,也不能说成是和阎锡山搞特殊的统一战线。当时我们为了争取阎锡山作为中间势力,仍留他在统一战线内,主动让出晋西南地区作为阎锡山驻军和吃粮地区。在此以后,晋西南地区地下党和广大人民同阎锡山反动政权进行殊死的斗争达六年之久。六年中都是由晋西区党委及以后的中共晋绥分局指挥和领导的。晋西南这一段地下党的斗争,理所当然地应载入晋绥革命根据地史册之内。我这篇回忆录,就是为了解决这一分歧意见而撰写的。在1989 年版《晋绥革命根据地大事记》中,已经把晋西南历史编入《大事记》。虽然不够充实,但说明《大事记》编纂领导同志,并没有接受上述错误意见。
在这个小册子中,有《五十年革命家庭纪实》一文,这是我妻桑一伟同志写的。我们的家庭是伴随着革命的过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和我的革命生涯息息相关,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因之就收集在一起。①
注:
①文中所讲收入本书的文章题目,有的已略改动。《五十年革命家庭纪实》一文已经抽出,桑一伟同志另外写了一篇文章,专门记述龚子荣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诬陷和经过斗争,最后获得彻底平反的情况。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子荣在“文革”中的劫难》。
(本站编辑:左丽)
主办: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晋ICP备15001143号-1
Copyright Shanxi Jinsui Culture Education &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9号院国投财富广场4号楼313/314 邮编:100073 电话:010-63395639/63395661 邮箱:sxjs9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