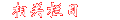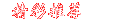
-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大力弘扬吕梁精神(06月21日)
- 悼念王军大哥(06月11日)
- “土窑泥坯”到军博(05月28日)
- 晋绥情怀和“智慧乡村”(05月23日)
- 2018年基金会工作回顾(二)(05月14日)
- 2018年基金会工作回顾(一)(05月09日)
- 贺大姐和红军后代到卢氏(05月08日)
- 军刀的故事(05月06日)
- 一位海军将军的期盼……(04月23日)
- 祭奠归来随想!(04月18日)
《我的回忆》 土改(二)
发布日期:2016-06-16 10:21 来源:《我的回忆》 作者:晋绥基金会
1947年3月,胡宗南奉蒋介石之命,进攻我党中央所在地延安。中央决定暂撤离,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前委,仍留在陕北指挥作战;以叶剑英为中央后委书记,组成人员有杨尚昆、李克农、李维汉、李涛等同志,带领后勤部、卫生部等三千二百人进驻临县。此外还有吴玉璋、谢觉哉和王明等,也驻扎在临县县城附近。以刘少奇、朱德等为中央工委,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土地工作会议,制定了《土地法大纲》,把《五·四》指示中不彻底的地方加以改正。
康生把极左风刮起来后,大约在当年夏末离开临县,但他带来的中央机关同志,多数仍留下继续搞土改运动。当时晋绥分局也派城工部长赵林为临县土改工作团团长,康乃尔为副团长,领导临县的土改。康生的“群众要怎么办就乍么办”,各村的工作组组长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是时为极左的最时髦的口号,也是整人于死地而后快的方法。此类事例很多:
一、赵林派我到五区管土改运动。我去到五单区委所在地白文镇后,在区上负责土改的县委组织部长李中林(1946年从新疆监牢获释后任成都市长,文革中受迫害而亡)和跟着康生去搞土改试点的临县县长杨万选要我去窑头村搞土改,杨说,夏征时他在窑头村把阶级成分全部划定了,浮财也没收完了,你去后开始斗地主就行了。吃完晚饭我在厕所解手时跟人说话,突然听到一个很熟悉的声音(二区区长刘万耀)但又以哀求的口吻说:“老冯,救救我吧,快冻死我了。”我问:“怎么回事?”他说:“把我关在看守所里时棉衣也给强行脱走了。”我回到李中林住处说:“有罪也不能冻着呀!”李一听,十分惊讶,马上通知一干部赶快给刘万耀把棉衣穿上了。1985年家乡召开老区建设座谈会,我应邀参加。刘万耀找到我,要求恢复党籍和工作。我问是怎么回事?他说:“不是你处理的吗?”我感慨地说,“快四十年了,还留了这条尾巴。”我当即去找与会的仍在职的副专员王德滋解决。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不包括土改时的问题。”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第二题的结尾说“……几乎一切‘左’的偏向都已纠正过来了。”还说没收的工商业也恢复了。这不符合事实。大约是1987年秋的一天,刘万耀来到我家,说他的冤案仍无人过问。我给当时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刘泽民一封信。半年后,刘万耀来信说党籍恢复了,每月给生活费十六元。二年后,其子来信,刘万耀病故了。
到底当时为什么把刘万耀实行双开除呢?他原是调去参加土改的,所在的村子是白文附近的卜家岩。一天,随康生来搞土改的中央机关同志要把一户中农定为富农,刘万耀提议再了解一下,结果引起对他的成分的怀疑。随即有人去四区小甲头(刘万耀家)村调查,查出他家有毛驴一头,于是便认为他是富农,而且包庇富农,就有了前述就脱掉他的棉衣并关押在五区看守所的事,当时他被开除了党籍和工职。其实,四区山庄人家大部分都养着毛驴,主要是因山上村庄无水,而在较远的山沟里才有水,大家都用毛驴来驮水。造成冤案的最简单原因就是是不搞调查研究,听不进不同意见。
我到窑头村后,当晚就有一个地主自杀。我看到在一个大院子里,有几孔大窑洞,都堆满了没收的浮财,包括家具、衣被、耕具等。我在贫农团会议几次提议分掉,免得雪打风吹损坏掉,但无人表态。
我在窑头村参加土改时间很短,但碰到两件事感觉处理得出奇,糊里糊涂,使我深感遗憾。一是由我宣布开除高有玉的党籍,当晚他就自杀身亡了。在我去该村前,高有玉已被划定为富农分子。稍说远点,高曾经为该村支书,后曾任区委组织部长,不知何时回到村里,也许土改开始后就免职了。二是要我在窑头村群众大会上宣布县政府判处窑头村恶霸地主刘三扬、刘秀书死刑,并立即执行。当我宣布完,除押来以上真正恶霸地主外,还押着高有玉的儿子,共产党员、县公安局股长高九丁也跪在临时的刑场,使我大吃一惊,但马上发出两声枪响,恶霸地主都倒地了,高九丁未被伤害。原来是有人背后安排要他陪刑。这完全是旧社会的做法。事后在县里,公安局长胡成奎对我意见很大,当面问过我:“怎么回事?”我当时无言以对。心里总觉得是我主持宣布枪决恶霸地主的场合上出现的强人所难的坏事。“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不是如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上批评的“笼统地提出了”“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实际上当时搞极左,害人的人,阴谋以左立功。祸根就在这里。
不久,赵林派警卫员把我叫回县里,原来是毛主席派胡乔木带来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小册子,我如饥似渴仔细阅读后,心里有了底,征得胡、赵同意(原来是送分局再印发),带着它骑自行车赶回村里,马上找了几个贫农代表宣读并与大家试划地富成分。大家听得入了神,老贫农刘世凯频频点头,新中农刘启启的眼睛显得很豁亮。有的说,“这样好的条条,你怎么不早说呀?”他们怪罪的很对。大家提议连夜把原划定的地富,除了刘秀书、刘三扬等外,都照文件一:一比对。按照当晚初步比对的意见,将以前已划定的百分之二十八降低到百分之八点六。随后我虽然被调走,离开了家乡。但我相信1948 年纠偏时,根据分局正式文件,划分的地富不会超过百分之五。当时天快亮了,代表还不走,有的说,“你几次提议研究分果实,我们就是不动手。”说明老区的农觉悟高,他们没有因果实多而有所动,他们深知斗争果实中有不少是阶级兄弟的劳动果实。刘启启原来很积极,但有一阵子话语变得很少了。那天晚上他显得特别舒畅,把心里话倒出来了。他说:“前些天,眼看快斗到我头上来了,心里憋得难受,现在没说的,干甚也不退缩。”
以上仅仅列举了在那种极左环境下出现的一些事例。真正的群众捍卫了党的路线和政策,采用了各种办法,保护了党的一部分财富一千部,维护了相当数量农民的劳动果实。说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本文来源:冯文耀著《我的回忆》本站编辑:左丽
主办: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晋ICP备15001143号-1
Copyright Shanxi Jinsui Culture Education &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9号院国投财富广场4号楼313/314 邮编:100073 电话:010-63395639/63395661 邮箱:sxjs9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