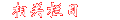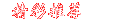
-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大力弘扬吕梁精神(06月21日)
- 悼念王军大哥(06月11日)
- “土窑泥坯”到军博(05月28日)
- 晋绥情怀和“智慧乡村”(05月23日)
- 2018年基金会工作回顾(二)(05月14日)
- 2018年基金会工作回顾(一)(05月09日)
- 贺大姐和红军后代到卢氏(05月08日)
- 军刀的故事(05月06日)
- 一位海军将军的期盼……(04月23日)
- 祭奠归来随想!(04月18日)
两个小八路的爱与憎
发布日期:2019-01-24 19:52 来源:山西政协报 作者:端阳生

王兴(1929—2019)
八路军120师六支队骑兵营老战士王兴同志,于2019年1月21日在朔州市怀仁县逝世,享年90岁。为铭记历史,缅怀先辈。从即日起我们网站将连载他的老战友王生明叔叔(笔名端阳生)的文章,以祭奠和追思晋绥抗日老前辈王兴同志。
两个小八路的爱与憎
——向绥蒙边疆进军的路上
1945年,只有11岁的我,已经在塞北军分区宣传队当了一年兵。另一位比我年长3岁的小战友王兴,已是具有3年军龄的老兵。这些乳臭未干的孩子兵到底能干些什么事?为什么数次精兵简政都没把他们减掉?
我能在10岁参加八路军,原因很简单:1942年8月5日, 在今山西省朔州市与偏关县的交界处,担任过我平鲁县城工部长和右南县委组织部长(当时李登瀛任县委书记),又调晋绥第五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科任科长的父亲王宝,被日特李占功等民族败类枪杀, 我母亲蒙青山拖儿带女,无家可归,生活无着落,就把我和我姐交给了五分区司令员郭鹏(中将)、参谋长刘华香(少将)、政治部主任陈云开(少将)。经军分区首长研究决定, 准许我姐弟二人接替父亲吃公粮,把我们送到供给部,由技术最好的裁缝,量着我们的身高给做了两套军装穿戴起来。从此我成为八路军的一个小兵。
小战友王兴,是山西省怀仁县吴家窑镇碗窑村的捏碗工人,其父王贵礼系我宋时轮支队地下交通员。1942年被本村窑主、汉奸赵丕成向驻扎在吴家窑碉堡内的日寇告密,被捕7天后惨遭杀害。时年11岁的王兴决心为父报仇, 瞒着母亲和小妹,瞒着村民,跑出两狼山,找到我雁北支队骑兵营,经营长王零余(英雄绰号王老虎)、教导员谷奇峰同志批准其参军。
1944年春天整风结束后。塞北军分区筹建宣传队,我与王兴被先后调来,成为同床战友。经过陈家营、黄树坪等大小战斗的洗礼,我俩关系更加亲密。

此照片摄于1945年冬,战声剧社部分指战员在绥蒙军区首府集宁(乌兰察布盟)合影。右起:王丽珍、刘兰芳、王兴、王玉梅、贺福龙、赵俊英。前排三人是:老红军杨福财叔叔左手挽王生明、右手挽王生梅。
1945年5月间,我患伤寒症在偏关县磁窑沟住医院。因连续6次“出水”,奄奄一息。7月间王兴来看我时,我正处在高烧昏迷状态。王兴问我想吃什么?我答:“想吃西瓜”。那时,我们没有一分军饷。王兴为了满足我临终前的奢望,不惜违犯军纪,到村外瓜田向瓜农讨了一个西瓜给我。谁都以为这是一颗送命瓜,出乎医生意外的是,正是这颗西瓜,使我第七次“出水”顺利脱险,由此转向康复。这年8月间,听到日寇投降的消息,王兴又来医院接我归部时, 再次交谈了为父报仇雪恨的老话题。这日,他用宣传队搞生产时买来的一头背高不足1.2米的小毛驴,把我接回宣传队驻地,做好向绥蒙边疆进军的思想和物质准备。几天后,接到出发命令,因我患伤寒病在医院躺了3个月,骨瘦如柴,无力行走,那头接我出院的小毛驴就成为我进军绥蒙的专用坐骑。
出发第一天中午在某村打尖,刚吃完饭我就感到困乏难支,立即在房东炕上熟睡过去。听得哨声一响,我朦朦胧胧起来,强打精神跑出门外,已见部队鱼贯出村。幸好,我的小毛驴乖乖地站在大门口等着我,由于它的帮助,我没有掉队。
部队行至关河某一拐弯处,因秋雨较多,这里水深至膝,大家不得不停下来解绑带,挽起裤脚涉水过河。我骑着小毛驴过河时,发现自己的双腿未打绑带,原来中午吃饭时解下绑带休息,因起身匆忙,把绑带丢在房东炕上。丢一副绑带不算什么,但与绑带一起丢掉的还有一袋手榴弹(3颗), 这可不是坐几天禁闭就可以了结的小事。想到如此严重的后果,内心惶恐万状。于是,我跳下驴背,把王兴叫到身边,向他通报了这一起“灾难”。他听了也是搓手跺脚。部队即将在前方老营镇宿营,何去何从,必须当机立断。
王兴见部队已经远去,他把自己的背包放在地上对我说:“把驴给我,你在这里死等!”
我望着王兴骑驴西去的背影,内心极度焦急,心想:要是我的房东不认账了怎么办?我们已是最后一批离开塞北抗日根据地的“杂牌军”,要是碰上近日已从陕西渡河,专门偷袭我零散军政人员的国民党顽固分子怎么办?遇到恶狼野狗挡住去路怎么办?想着想着,天色已暗,对自身可能被狼吃的恐惧,代替了对王兴的忧虑。好在距河边10余米处有一棵小树,我只好爬上树杈等待王兴的归来。
等呀等,蚊虫在周身狂叫,流星在苍穹滑翔,也许这个世界会永远这样寂寥下去……
啊!有了希望,终于听到我那小毛驴急促的蹄声由远而近。河对岸,王兴压低声音喊了两声:“生明!生明!”
我尖叫了一声,从树上滚爬下来,扑到亲爱的战友怀中。我俩同骑着极有耐力、极其友好的小毛驴,在天上的银河与地上的关河岸上漫游了约一个半小时,才赶上已进入梦乡的部队。
我们这支不文不武或半文半武的留守部队,踏着八路军120师健儿们的血迹,曾在日寇刚刚逃离的平鲁、清水河、左云、右玉、凉城、新堂、大土城、丰镇停留。当我们从丰镇坐火车到我绥蒙首府集宁之时,令人惊异、使我沮丧的事发生了——王兴失踪。有人说,王兴开小差走了。我除了惊异、失望,还有难言的焦虑,就是王兴把我携带的3颗手榴弹带走了,出了事他和我都会受到军法的制裁。幸好谁也没有提及手榴弹的事。部队到集宁驻防半月之后,王兴突然返部。领导说要开会斗争他。王兴在“斗争会”上拿出一身血衣,讲述了他离队之后的经历。他首先承认,自己犯了擅自离队的错误,但不承认开小差,更不承认所谓“脱离革命”。他说他干了一件他认为必须干、应该干的“公事”。
王兴说,自从听到日寇投降的消息,他就恨不得插翅飞回故乡。他参军出走那天,曾为母亲担满一缸水,这缸水该早吃完了,他的母亲和年幼的小妹,是否还活在世上?这个问题折磨得他无法忍受。他还担心他的仇人赵丕成,会跑到大同或归绥(呼和浩特)躲藏起来,杀父之仇报不了,如何向母亲交代?
于是,他身穿军装、携带3颗手榴弹离开部队,独自南下,向怀仁县吴家窑方向走去。
此时,日寇投降不久,依仗日寇胡作非为的汉奸、恶棍变成丧主之犬。王兴的仇敌赵丕成正准备打点行装,逃往大同。
不料,深夜有人敲门,一位手提手榴弹的少年八路,突然出现在赵丕成面前。王兴身后虽然只有两位本家侄叔相伴,但时局突变,赵丕成不敢有稍许抵抗。仇人相见,不寒而栗。
“是双娥(王兴的乳名)回来啦?”
“是我!你起来跟我走一趟!”
赵丕成见王兴拿着绳索走近,便转过身去,让王兴紧紧捆绑起来。第二天,王兴在镇上找到一名我方工作人员,在该同志的帮助下,有关乡亲与赵犯面质了其出卖我地下交通员王贵礼同志的罪恶事实。在人证和物证面前,赵犯对其罪行供认不讳,要求以其全部家资抵罪。王兴则说:“我的母亲和小妹正在饥寒交迫中,急需花钱买药购粮,但我不能出卖我父亲的鲜血度日。你欠我什么,就用什么偿还吧!”经群众大会公审,王兴举起正义的钢锹,当众向这个民族败类讨还了血债!
1952年,在镇压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中,我正在成都空军某部工作。一日接到原察哈尔省尚义县人民法院来函。函曰:“王生明同志:今寄去叛变杀人犯李占林(原名李占功)之判决书两份,我院业经报省主席于1952年11月20日批准李犯占林死刑,当日午12时将该李犯占林由监提出验明正身即绑赴本县城东刑场执行枪决,确已气绝身死,今备便函通知给你,希你安心为人民工作为盼。”
去年,我去雁北小峪煤矿,拜访了老战友王兴。他已从党的纪检工作岗位上退下来,过着离休干部的生活。回首往事,我俩值得对后人言谈的事不多。唯民族仇恨,不可不讲;民族气节,不可不扬。否则,将有国破家亡之患。故而在此一谈。
(发表于1992年《山西政协报》)
本站编辑:杜瑞
主办: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晋ICP备15001143号-1
Copyright Shanxi Jinsui Culture Education &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9号院国投财富广场4号楼313/314 邮编:100073 电话:010-63395639/63395661 邮箱:sxjs9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