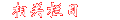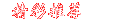
- “土窑泥坯”到军博(05月28日)
- 晋绥情怀和“智慧乡村”(05月23日)
- 2018年基金会工作回顾(二)(05月14日)
- 2018年基金会工作回顾(一)(05月09日)
- 贺大姐和红军后代到卢氏(05月08日)
- 军刀的故事(05月06日)
- 一位海军将军的期盼……(04月23日)
- 祭奠归来随想!(04月18日)
- 祭父亲(04月16日)
- 祭扫先烈有感(04月15日)
千里归队征途难
发布日期:2016-01-18 14:30 来源:《吕梁晚报》 作者:晋绥基金会
每当我看到这些照片,就会想起母亲的艰难经历,总会泪水涟涟。母亲从1946年7月(时年25岁)至1947年7月所经受的磨难是现代年轻女子无法想象和承受的。但是母亲凭着执着的革命信念和坚强的毅力、凭着她对党的信任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挺过来了。
1945年7月,359旅南下第二支队奉命出发,父亲为717团副政委,将随团出发,去南方开辟和建立新的根据地。上级专门在延安北关组建了家属学校,任务是带好孩子们——革命接班人。母亲在回忆录中详细记录自己随359旅家属队赴东北找老部队的亲身经历,字里行间流露出经历艰辛的心酸以及最终获得胜利的喜悦。
书文如下:1947年7月,母亲与父亲分别两年后在勃利重逢后的合影。母亲带着兄妹二人,随同359旅家属学校从延安出发,长途跋涉抵达东北时儿子黎辉3岁,女儿额红2岁。
再困难也不能把孩子丢掉
抗日战争胜利后,胡宗南进犯延安。1946年7月,正值盛夏,家属学校奉命整装出发,到东北找老部队去。我25岁,有两个孩子,儿子刚会走,由于没奶吃,身体羸弱;女儿才8个月,刚会爬,带他们上路实感吃力,曾想把女儿送人,但是一来战争混乱,怕将来再也找不到孩子。二来老乡的生活条件更差,最终我打消了这个念头,决心不丢掉孩子,要忍受一切艰难困苦把他们带出去。

1945年6月,父母分别前在延安拍的全家照。
学校给每个孩子做了一张小木床,两个小床跨放在骡子背上,一床被子披在骡子背上,大人还可以骑走一段路。到了黄河边没有骡子使用了,只能向乡亲们借用大牲口,大多是驴子、牛和马。最不听话的是驴子,每当骑到驴背上,它会突然撒欢地跑上一段路,然后突然卧倒在地,让人措手不及,身体也会从驴脖子上滑下来,狠狠地摔在地上,狼狈极了。
有一次,驮着两个孩子的那匹马来到一片树林边,突然受惊,又蹦又跳,眼看两张小床摇摇欲坠,孩子们的性命危在旦夕。我急得大哭,大喊救命。幸亏从外面跑过来两位老乡拼命拉住了马,才避免了一场灾难。
第一次脱离大部队
夏季酷暑难耐,每到一站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一个孩子的母亲可以抱着孩子到街上买吃的去了,而我要照顾两个幼儿,尤其儿子肠胃不好,常常拉肚子,弄得被褥极脏。我需到处找水清洗,还得想办法做饭吃。女儿还不老实,在炕上乱爬 ,不知道从炕上掉下来多少 回,真是顾了东来顾不了西。行军路上易上火,我们娘仨都得了急性结膜炎,眼睛红肿流泪,疼痛难忍。可在黄土高原上没有水清洗,更没有眼药水治疗,只能坚持行军。眼睛痛得睁不开,流泪不止,怕光怕热。后来我和女儿的眼睛终于慢慢好起来了。儿子的眼睛却一直不见好,又红又肿,痛得他用头撞墙,不停地啼哭,哭的得了小肠疝气。看他那样,我心如刀割,暗自落泪。等我们到了张家口,儿子的眼疾已经很严重,睁不开眼睛了。
这里是晋察军区的所在地,白求恩医院设在张家口附近,我决心留下来先给儿子看病。到军区说明了我的实际情况后,组织上派了一位男同志帮助我抱孩子去医院。家属队的同志们先走了,就留下我们娘仨,这是我们第一次脱离大部队。我急忙赶到医院,先给儿子看疝气。医生见状,立即采取措施,在他的疝气处抽出了一大管子液体。到眼科,医生还指责我为什么拖延这么久才带孩子来看病,说再晚些孩子的眼睛就要瞎了。自此我们在张家口停留了十几天,那位男同志每天背着我儿子到医院眼科换药,儿子的眼睛才慢慢好起来,他的小肠疝气自那次抽液之后就好了。先走的同志们在多伦没有过去,又被绥远傅作义的骑兵冲散阻拦,过不去了,她们又转回了张家口,我和学校的校友们会合在一起了。
第二天张家口告急,我们急忙撤退,坐火车到冀西。撤退时显得有些忙乱,我把两个孩子放在小床里,专等火车到来。火车一到,大家一哄而上,我把第一张小床搬上火车后火车就要开动,来不及下车去搬另一张小床了。说时迟,那时快,一位同志飞也似地帮我把小床搬上了火车。多么感激那位好同志呀,他的帮忙使我们娘仨没有分离。
第二次脱离大部队
几个月的行军,加上两个孩子的拖累,让我感到心力交瘁。到了冀西 ,离我娘家
(河北定县西城村)就不远了。我决定回家休整一段时间,到家已是1946年的秋季。其他校友们直接去了山东惠民,这是我们娘三个第二次脱离大部队。
离家时我是一个年轻姑娘 ,回来时却带 了两个孩子。多年毫无音讯的人突然回到家乡,乡亲们都很震惊,纷纷来看我,仿佛我从天而降。村中说什么的都有,我全然不顾。只为带好这两个孩子。父亲把二姑(姑父也在革命部队中,时为定南县武工队负责人)接来与我做伴,她也带着一个孩子,就一起养。当时正值冀中大旱,粮食十分紧缺,有些村干部家常有揭不开锅的现象,但村里的党组织和民主政府把我们作为军属看待,对我们很优待,每天供应我们母子三斤小米,我真感到惭愧。这些粮食再掺上点菜叶,全家人还算过的去。
第三次脱离大部队
1947年春节刚过,359旅派两名战士来接我们了。村中老人劝我说路程遥远,带着两个小孩子上路太难了,不如在村里找个人家过吧。我不听他们的胡言乱语,一定要把革命后代交给革命的队伍。没有路费,我毫不犹豫脱下手上的戒指交给了父亲,让他变卖充当路费。
山东寒冬,条件更艰苦,冷屋凉炕,什么都得靠自己动手。女儿的耳朵染上了黄水疮,不时用手抓,吃奶时又抓我的乳房,我不幸感染了急性乳腺炎。乳房又红又肿,里面化脓疼痛钻心,让我难以忍受。没有消炎药,部队又要出发了。我忍着疼痛跟随大部队前行,一路上后勤的老龙同志(江西籍的老红军)帮助我照顾孩子们。我坚持坐大车到了烟台,开始还可以勉强支撑,可是乳房越肿越大。一到宿营地,躺下就动弹不得了,全靠老龙同志前后照应着。
大家把军用品全部丢掉,化装成老百姓,从烟台坐小汽轮一夜偷渡到大连后我就奄奄一息了。359旅的廖英杰同志当时任大连的卫生部长,见家属队到了,来看望大家。听说我病重,立即把我送进医院,当天下午就动了手术,切开两个口子,放出了脓血。开刀后我马上有了精神,也可以吃下东西了。孩子们和我一起住进了医院。每天换药,真够疼痛的。
真是祸不单行,女儿不小心在医院的电梯里把手指碰破了,得了破伤风,高烧40多度。这家医院治不了,又被转送到大连医院。一位外国大夫看过病,打针吃药后说:如果今晚退烧,她的前胸后背出一身疹子就好了。果然到了晚上,她出了一身的疙瘩,退了烧,度过了鬼门关,母女平安无事了。由于我乳房上的伤口未愈合 ,其他的家属均已 先行,顺利抵达东北。我们四人(包括老龙)在大连多逗留了一个来月,这是我第三次脱离大部队,单独行动。
终于和老何团聚
部队再次派人到大连来接我们。我已痊愈,正准备上路,须先乘船赴朝鲜平壤,然后绕道去东北。我们先乘苏联货轮,我抱一个,老龙抱一个,爬上高高的舷车站。在那里有卖朝鲜的粘团子,我们买了几个吃,真的美味可口,至今余味未尽。
去东北乘坐的是拉货的闷罐车,车厢里又挤又闷,车门一关,又黑又不通气,无法睡觉,真够难受的。两个孩子需要吃喝拉撒,衣服脏得要命。火车的速度比大车还慢,从平壤到图们 ,这 列闷罐车足足走了一个礼拜,因为这列车不是正常客车,常常要给别的车让路,走一段之后就被摘下搁置在一旁,不知经过多长时间才又被挂上前行。就这样走走停停。车一停,就得给孩子们弄点吃的,给孩子们洗衣服,不然车一开就闷在车厢里受罪了。好容易到了图们,下车后又坐上了大车,几天后终于到了东北勃利,这里是359旅(东野独立一师)部队的后方驻地。1947年7月,我和孩子们到达勃利时 ,老何还在前方执行任务, 时任东北民主联军独立一师政治部主任。见到他时,我几乎认不出来了,他受伤后大病了一场,消瘦不堪。原来7月初他在执行接新兵的任务时,在蛟河火车站为了照顾新兵上车,自己却晚了一步,火车开动才急忙登车,结果踏空掉了下去,车门撞在肋骨部位,受了严重的内伤。幸亏一位同志手疾眼快把他拉上去,不然就提前见马克思了。他一直躺在闷罐车厢的地板上,没有任何药物治疗,三天三夜高烧不退,坚持完成接新兵的任务返回勃利,我们才得以团聚。虽然父亲不认识自己的女儿,认识的儿子也经受了两年的分离,但我感到骄傲。

傅俊杰穿空军服装照
傅俊杰简介
傅俊杰同志(1921.11—1998.11), 河北定县西城村人,少年受到共产党的影响,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冀中军区八中和华北联合大学学习、工作。1941年6月,从白求恩医校参军,成为一名正式的八路军战士。1943年3月,随同白求恩医校奔赴延安,路经陕北延安延川县临真镇后即参加120师359旅717团工作,任团政治处组织股干事。在延安期间,参加了整风运动、南泥湾大生产运动。
1946年6月,随第二批南下359旅的家属大队从延安出发,历时一年多,克服艰难行程5千公里抵达东北牡丹江勃利县归原部队。后曾任双城制鞋厂(军工)支部书记,1949年后任辽东军区政治部直属机关协理员,东北空军政治部党务科长。1951年被选派进中国人民大学进修班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刚组建的建设部工作。不久调回部队,负责北空保育院的筹备工作,后任保育院政委。1954年转业,历任北京工业学院人事处干部科长,北京空军育翔幼儿园院长,北京空军育翔小学校长,北京西城区育翔小学校长,北京西城区教育局巡视员等职,正局级待遇。
傅俊杰同志在教育战线多年努力耕耘,荣获北京市教委为表彰从教25年以上的杰出教职员工所颁发的“园丁荣誉纪念章”。
主办: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晋ICP备15001143号-1
Copyright Shanxi Jinsui Culture Education &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9号院国投财富广场4号楼313/314 邮编:100073 电话:010-63395639/63395661 邮箱:sxjs9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