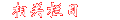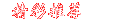
- 有这么一批《晋绥日报》的传承人(07月10日)
- 浇开中朝友谊之花(07月09日)
- 有一种记忆叫怀念……(07月08日)
- 有份爱心来自大唐(07月04日)
- 播撒慈善的种子(06月28日)
-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大力弘扬吕梁精神(06月21日)
- 悼念王军大哥(06月11日)
- “土窑泥坯”到军博(05月28日)
- 晋绥情怀和“智慧乡村”(05月23日)
- 2018年基金会工作回顾(二)(05月14日)
记忆中的父亲
发布日期:2017-01-05 11:30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作者:林梅梅
林梅梅
母亲说,父亲生性沉默,除了喜欢看书,就是喜欢孩子。然而在我的儿时记忆里,父亲好像并不喜欢我和妹妹双双。他老是那么严肃,老是对我们不满意。我很怕他。
1945年9月,父亲奉毛主席的指示带着干部团从山西去东北。由于路上要过敌占区,很危险,中央指示不准带孩子。父亲和母亲决定忍痛把3岁的我和10个月的妹妹双双留在河北省涿鹿县我母亲的老家。

1945年9月,林枫、郭明秋与女儿梅梅、双双即将分别时,摄于山西兴县北坡村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窑洞前。
进军东北的途中,母亲在宣化把我们交给了来接的表舅。据母亲说我因为贪吃表舅带来的一块饼,就让人家抱走了。我不记得这些了,只记得我后来找不见母亲时那撕心扯肺的哭喊,哭得累得睡着了,醒来接着哭,可是再也看不见母亲和父亲了。60多年了,那情景还会在睡梦中出现。1948年10月,父母亲派人把我和双双接回了他们的身边。在与父母分开的这3年里,大部分时间我住在母亲的后奶奶家里,受尽了虐待,天天想着回到母亲身边。可是当我们在哈尔滨火车站重逢时,已经不认识他们了。双双的寄养家庭没有告诉她有自己的亲生父母,所以回到哈尔滨后,双双经常宣布“这里不是我的家”,要回到“我自己的爸爸妈妈”家去。双双每次说这句话时,母亲就伤心地流泪。回来以后不久,1948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我们全家来到沈阳,我和双双直接进了位于北陵大院里全托的东北人民政府机关小学和幼儿园,很少有机会见到父母。

儿时的林梅梅
那时候东北刚解放,百废待兴,父母顾不上我们。幼时和父母分离造成感情上的隔阂时时影响着我们,尤其当他们严厉地批评我们的时候,就以为他们不喜欢我们,越发躲着他们。星期六,他们派人去学校接我。我就藏在床下边不回家。有一次在饭桌上父亲看着双双,慈爱地挑起左眉向她笑。很少见到父亲的双双不知这是什么意思,竟吓得哭了起来。父亲也很没趣儿地走开了。母亲说其实父亲挺喜欢双双。双双几个月的时候在父亲身上爬来爬去。父亲看着她说:“这孩子将来忠厚。”当时,我的很多同龄的朋友们都有类似的经历。我们痛苦,父亲母亲更痛苦。有次我给母亲讲我小时候在后太姥姥家过的悲惨生活时,她说:“你活下来了,这就不错了!”我知道母亲的意思。我的两个姐姐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条件下都没有能活下来。多少年了,直到母亲去世前,她还是一提起我那两个姐姐就难过,经常念叨着:“要是你红儿姐活着的话……”“要是你龙生姐活着的话……”等。长大以后,我慢慢理解了这是老一辈革命者们为了救国救民所做出的牺牲和付出的代价。

小姐妹--林梅梅和林双双
我和父亲最大的一次冲突是在1960年的暑假。那年,我18岁,刚刚结束了紧张的高考。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可真是松了一口气。父亲母亲去北戴河参加中央在那里召开的会议,也带着我们去了。我就和朋友们玩“疯了”。父亲母亲很怕这样优越的条件会惯坏了我们,天天逼着我们写大字、读报纸、学做鞋、纳鞋底子、早晨5点起来磨豆浆、帮着工人拔草……我很不愿意做这些事,常常溜出去和朋友们玩。父亲发现了几次后,终于“火山爆发”了。他整整“骂”了我3天,而且上纲到“革命与反革命”的线上。他说:“少奇同志说‘以前是反革命的老子有革命的儿子;现在有可能是革命的老子有反革命的儿子’!”“你18岁了,整天还是玩,玩,玩。你妈18岁的时候已经在领导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了!你看看外边那些干活的农民。他们在18岁的时候要干活养家,他们能玩吗?”“干部子女条件太优越,脱离群众,很危险!”“你是干部子女,条件比别人好。你就应该利用这个条件努力学习,学成全班最好、全系最好、全校最好,你才对得起人民给你提供的这个条件。”等他“骂”够了,转身往外走时,还重重地说:“你到底走什么路,你自己决定,我没有时间和你没完没了地这么说,我还有6亿人的事要照管呢!”
我被他“骂”得哭了好久,心里觉得很委屈,并不真正理解为什么他那么生气。暑假就是“玩”的时候,怎么会扯上革命不革命呢?过了这么多年以后,现在回想起这件事,看看这些年来在一些子女中发生的问题,才开始理解那时父亲思想中深深的忧虑。
尽管我那时并不真正理解父亲,但那次的批评在我思想上造成了压力。我在清华学习很努力,一方面是由于清华良好的学风影响,一方面也是心里在和父亲赌气,心想我就要学一个全班最好给你看看!我在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学习的头3年正碰上我们国家的困难时期,常常吃不饱饭。但我仍然刻苦学习,到四年级时,我的主科成绩全是5分。被列举在当年中央的一份有关高级干部子女学习情况的报告里,其中特别点名表扬的3个人中,我是其中之一,那时我才看到父亲的脸上有了一个浅浅的笑容。
“文化大革命”中,一夜之间,我的父亲被打成了“黑帮”,我很不理解。那时候,我对父亲还没有很深的了解,但是我深信他是一个正派人,是一个对党对国家忠诚的人。他对自己子女那样严格要求,不可能是装出来的。
在大字报中,我才了解到,父亲在东北工作的时候曾经在是否进占大城市的问题上和林彪、高岗有过激烈争论。父亲和彭真、吕正操等人认为现在敌我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进占大城市;而林彪等人则要求我们从已经占领了的大城市,如哈尔滨、绥化等地退出来。父亲以前从未告诉过我们这些事。1966年8月,这个事被翻了出来作为我父亲反对“最高副统帅”的罪行。虽然当时我很崇敬这个“副统帅”,但知道父亲被斗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就想,不管在这个问题上谁的意见正确,也许我父亲和彭真对,也许林彪对,我搞不清。但我认为这是正常的军队领导、党委领导内部的争论,就为20年前的这么一个不同意见,就在自己得势以后把人家打成“反党”,林彪的心胸也太狭小了!我这样想,也就这样说了出来。于是我也就被打成了“反动学生”,在学校里被斗争了几次,不分配工作,在军垦农场和清华大学监督劳动了3年。
后来从大量揭发出来的材料中得知,林彪的确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明确示意康生:解放战争时期林枫在东北反对过他。康生立刻心领神会,让他在中央党校的心腹造反派头子连夜写了大字报,把这件事公布出来。狂热中天真无知的群众就在第二天把我父母批斗了,在党中央的最高学府里游街,极其残忍地进行肉体摧残和人格污辱。父亲成了“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遭受肉体批斗、人身污辱、当众被游街示众的中共中央委员。学校里贴满了“谁反对林副统帅就砸烂他的狗头!”的大标语,满北京城到处是所谓的“林枫反党十大罪状”。
我们最后一次听到父亲的音讯是1966年12月18日北京工人体育场的批斗大会后。北京几所大学的造反派组织联合召开批斗大会,声称要“血染十八块”,即十八个他们所谓的“黑帮”分子、“三反”分子,其中除我的父亲外,还有北京市市长彭真、彭真的夫人张洁清、北京市副市长刘仁、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等人。我的朋友们亲眼目睹那次残酷的斗争会以后,惊骇得许久不敢告诉我们详情,只说我父亲因为不肯跪下,被打得很厉害。想到父亲原来就有心脏病,我们都很担心他的生命安全。有一次,在大街上随处散发的小报上我看到康生的一次讲话,康生说:林枫借口胳膊被打断了,就不写交代材料。有人说,父亲在301医院治胳膊,弟弟炎炎就打扮成红卫兵到301医院去找父亲,没有找到,以后就再也没有听到父母的消息了。
1972年8月5日,我们被允许在秦城监狱会见父亲。6年来,他老人家音信全无。突然知道他还在世,我们姐弟几个都很兴奋。但当我们在秦城监狱见到他时,谁也不敢相信这位骨瘦如柴、目光呆滞的老人就是父亲。从秦城回到北京后,我们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请求让父亲出来治病,而且允许我们姐妹照顾他。几天以后,毛主席批准了我们的请求。父亲被送到阜外医院就医。那时,他还没有解除监护,当时的“中央专案组”让秦城监狱的看守和父亲同住在一个病室内。阜外医院内科的主治医生郑德裕大夫是个很有正义感的人。他是吉林医学院毕业的,在东北时曾听过我父亲讲话,对老一辈的革命家很有感情。他对专案组的这种作法很有意见,以一个医生的身份对专案组说:“林枫的病情很严重,有生命危险。你让看守和他住在一个病室内。他就紧张,睡不好觉,病情就会恶化。要是死了人,毛主席的批示就白批了。”专案组没有办法,只好让看守搬到对面的病室内,而允许我们姐妹晚上守在父亲的房里。我那时觉得郑大夫真是了不起。他敢这样和专案组作斗争。父亲在阜外医院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5年。在他生命垂危、气管已经切开而无法发出声音的时候,他用嘴型对阜外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们说:“谢谢你们!”
看守搬走了以后,我们姐妹几人就轮流陪夜。第一个晚上是我陪的,父亲很兴奋。6年了,他听不到外面的真实消息,连林彪出逃的事也是前几天在秦城会见时我们悄悄告诉他的。他不停地说呀、问呀,而且声音很大,护士长几次来告诉我们说他把整个病房都吵醒了。我也几次提醒他不要再说了,但他就是停不住。后来专案组也听说了,专案组的人跟我说:“你父亲是个5分钟才说一句话的人,怎么现在突然话多起来了?”我把这话告诉了父亲,他低头不语,半天才说:“5分钟一句话,6年下来也够说几天的了。”
从1972年8月到12月底,父亲一直处于一个犯人监外就医的状态。专案组的人要我们保证,除了我们姐弟几人及医护人员外,其他任何人不许进病房和我父亲交谈,否则我和父亲就要承担一切责任和后果。那时有些老同志听说了我父亲住在这个病房,就找到这里来看望他。我非常紧张,赶紧请他们出去。看到这种情况,父亲和我说:“专案组不是说,主席批示‘放他出来治病’吗?你去问问他们,这叫‘放’吗?这也没有‘放’呀!”当我用这个问题去问专案组人员的时候,他也没有否认现在确实没有“放”,但他振振有词地说:“主席说的话多了,毛主席批了的也得有政治局通过!”这话在一般情况下听来也没错,但在当时那种形势下,一个办案人员敢这样说话,确实也说明了当时政治形势的复杂。他仗着有康生和“四人帮”作为后台,就这样嚣张。看到这种情况,我就没有回贵州工作,而和姐妹们守在父亲身边。这4个月里,我几乎天天去医院,即使不是我的班我也想去。和父亲朝夕相处的4个月,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我第一次发现父亲一点儿也不可怕。他非常慈爱。父亲以前总是忙工作,或是看书,没有时间和我们谈话。现在他没工作了,眼睛也坏得无法读书了,每天下午他就坐在床上和我们聊天,从他午睡起来一直聊到夕阳西下,从北京大街上卖的烧饼夹酱牛肉一直聊到他幼时东北老家的生活。他有声有色地告诉我,他小时候怎么偷吃他十三叔地里的瓜。我简直不能想象我的父亲小时也曾经这样顽皮,还干过这种事。有时候我们谈到母亲,他说:“你妈呀,就是爱说。一说起来呀,黄河开了闸,挡都挡不住!”父亲说得那么形象,逗得我大笑不止。
父亲的头脑非常清楚,与世隔绝了6年,很快就跟上了形势。老百姓的反映告诉他。他很快就能做出正确的分析。以前他很遵守纪律,从不和我们讲党内的事。现在党内的这些事都在大字报、小字报上公布出来了,我有疑问的地方去问他,他就耐心地给我讲活党史。由于父亲熟读古书,他讲的时候都是引经据典,听来很有意思。父亲看到我们经过了这几年的磨难,比过去懂事了,成熟了,能给他办事,甚至能和他深入地讨论重大政治问题了,也很欣慰。所以在1972年10月母亲刚放出来的时候,为了让母亲早些跟上形势,他让我带话给母亲:“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让母亲向我们学习。
父亲很高兴我们给毛主席写信救他出来。他说,他如果现在还在监狱里,绝不会活到年底。郑大夫说父亲的病很难治,因为他同时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肺病和糖尿病。治肺病需要营养,治糖尿病又需要控制饮食。医生首先给他定高蛋白饮食增加营养。但是他吃不下去,吸收不了。我们只好从家里给他做小米粥、红豆粥、东北的高粱米饭、酸菜等送到医院里。父亲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经常有小腿痛,有时疼得呻吟一夜,闹得我也睡不成觉。我就买了艾卷来给他熏脚心。那时我正怀孕,夜里一边给他熏脚,一边打瞌睡,一不小心,艾卷碰到他的脚上,我吓得要命。点着的艾卷有300℃的高温!但是父亲竟然一无所知,毫无反应。我去问医生这是怎么回事。郑大夫说:这是全身末梢神经炎引起的,脚底部末梢神经坏死。末梢神经炎是典型的监狱病,一般由于长期缺乏阳光和新鲜蔬菜,长期缺乏维生素所导致。脚底部神经末梢坏死使他走路时不稳,他已无法感知是否踩到了地面。
我问父亲,是不是在监狱里他每天的饭不够吃。他说:“是没法吃,因为饭里满是沙子”,而且就连这样的饭菜也是从门下的小洞中推进来的。到后来,全身关节炎发作,他的腰疼得弯不下去,拿饭菜非常困难。他说:“我要是再给送进去,就活不了了。”我说:“爸,你要是再给送进去,我就要求一起进去,替你拿饭菜!”父亲说:这些年来,生活上的恶劣条件都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那种精神上的压力,把你打成反革命的那种精神压力。六年里,他就是在这个革命与反革命的线上斗争。
1966年底,他从党校被带走以后,开始是和罗瑞卿、刘仁等一些老干部关在西郊罗道庄的一处卫戍区军营里。他和毛主席原来的秘书叶子龙叔叔关在一个房间,但不许互相说话、接触。那时不允许他看报纸,但叶子龙叔叔可以看。有时有重要消息了,叶子龙叔叔就对着父亲把报纸举得高高的,让父亲能看见大标题。1968年3月一个寒冷的下午,一帮人进来把他从屋里提了出去,让他站在寒风中,对他宣读了正式逮捕令,宣布他为反革命。父亲说当时他的脑子“轰”地一下,再讲什么也听不见了。尽管他有丰富的党内斗争经验和充分的思想准备,他还是没有想到他会被正式地宣布为“反革命分子”,被正式逮捕!
父亲讲到这里停了下来,默默地看着我。我点点头,明白他在说什么。父亲说,以前他理解一个共产党员会坐国民党的监狱,不能理解一个共产党员会坐共产党的监狱;现在他理解了,一个共产党员也会坐共产党的监狱。
父亲说:即使在监狱里,也会碰到好人帮助他。父亲常会回忆起在监狱里负责送饭的一位老人家,他有时会悄悄到外边去摘一两个新鲜西红柿送给父亲。有一次父亲得了感冒,发烧,那位老人偷偷地给他的饭里放了一个鸡蛋,一块酱豆腐。父亲觉得那是他一生中吃得最香甜的饭菜。我也告诉父亲这些年来也有不少群众帮助我们。我在学校挨斗的时候,我们班上一个同学偷偷地来告诉我,他们跟着斗我是不得已。其实我说的那些批评林彪、江青的“反动话”,他们晚上在宿舍里关上门说得比我还厉害。在我生活最阴暗的时候,这些话给了我一线希望,让我有勇气活下去。这件事会让我记一辈子。“文化大革命”中,弟弟被谢富治点名抓进监狱。我们几个姐姐都被分到了外地。家里只留了一个十来岁的小妹妹星星,隔壁邻居和平里1区5号楼9单元一层的一个穷苦老太太就经常主动照顾她。这位老人家给星星一节一节地加长她的棉衣,还叫她到家里吃饭。我们永远感激这个好心的老奶奶。
我有时和父亲谈到江青一伙人的倒行逆施、专横跋扈,心里很着急。父亲却认为那伙人长不了。他说:从年轻时起,他就建立了一个信念:任何人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不管他一时间怎么不可一世,最终都会失败的。我告诉他,很多人暗地里在和江青一伙做斗争。他很兴奋,但他又说:“投鼠忌器。”
父亲常告诉我们要“沉下心来想问题”,“不要跟着风走”。他和我说:“不要说很多话,要说一句话。”我明白,他是在告诉我,要把问题想透了再说话,只有把问题想透了,才能一句话点到实质。记得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北京市全天停课、停工打麻雀,我领着弟弟妹妹兴奋地爬到房顶上大喊大叫轰麻雀。父亲从屋里出来,厉声叫我们马上下来。他的脸色非常严肃,但又不讲任何道理。我当时很不理解父亲为什么是这种态度。这个谜到很多年后才解开了。父亲每当看到我们处于这种盲目的狂热状态时,就会很。有一生气地说:“你们呀,就是要刮风、刮风!”
我们姐弟共6人,我和弟妹们在家里回忆小时候的生活,提到1960年暑假父亲骂我3天的事。父亲曾说他有6亿人的事要管,没时间跟我多说。弟弟炎炎开玩笑地说:“现在没有6亿人的事了,只管6个人吧”。我把这话告诉了父亲。他沉思了半天,抬起头来严肃地说:“告诉炎炎,6个人的事和6亿人的事一样,都是很重要的!”
父亲确实非常注意对我们的思想教育。“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姐弟6个都有过坎坷的经历。有时,对一些错误地对待过我们的人有情绪。父亲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就对我说:“你要给妹妹做工作,让她明白不应该对这些人有情绪。如果我直接和她说,她会伤心,因为她确实在‘文革’中因为我受了委屈。可是这些人只是普通群众,他们是跟着错误路线走的。如果我们的队伍在每次路线斗争之后就分裂成两半,那么这十次路线斗争之后,我们不是就分裂成20片了吗?张国焘路线之后不是就走了一个张国焘吗?高岗事件后,中央让我出头解决高岗集团的处理问题。我见到高岗的秘书,他是一个青年,他知道什么?还不就是执行高岗的指示吗!我就给他很好地安排了。那些所谓‘高岗分子’,只要是对高岗问题有认识,我都给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让人家有改正错误的机会。”
解放初期,王光伟叔叔曾任东北人民政府秘书长。他有一次对我说:高岗在东北时让林枫同志分管抗美援朝支前工作。可是高岗处处刁难林,给他出难题,手段非常恶劣。我们在下面工作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非常生气。但林枫却总说:“不要说,不要说,大局为重。”王光伟叔叔说:“林枫同志就是领着我们埋头苦干。那时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困难可想而知。林枫同志根据周总理的指示,领着我们组织生产,调集物资,安排运输,极端紧张地把大批粮食和物资及时运到了朝鲜前线,有力地支援了前方将士。同时我们还要对付美军的空袭和细菌战,接待和安排从前线下来的大批伤病员,真是夜以继日地干。东北人民为抗美援朝做了极大贡献。因此高岗也挑不出我们什么错来。”他感慨地说:“所以为了大局,经常要忍辱负重啊!”
一些在东北工作过的叔叔告诉我,尽管我父亲在东北工作时期受到高岗的压制,但在处理高岗集团问题时,他对于那些一度跟着高岗走的同志却没有落井下石,泄私愤,而是本着团结大多数干部的精神,宽宏大量地来处理,使那些同志中的不少人在认识了错误以后,又给国家做出了很多贡献。这件事在党内影响很好。父亲在阜外医院住院时,高岗事件已过去20多年。一些当时受到高岗事件牵连的同志后来走上了新的岗位,有的已经在新的岗位上干得很有成绩了。知道我父亲从监狱里放出来的消息后,他们还到阜外医院病房来看过他。现在,在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以后,看到了和听到了许多在党内斗争中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恶劣后果,更加感到父亲宽阔的心胸和顾全大局的精神是多么难能可贵。
那时候,父亲和我谈得很多的一个话题是他抗战八年在山西的生活。那段时期,他第一次和毛主席有了直接接触。父亲对毛主席对晋西南、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指导很佩服。父亲和贺龙、关向应等领导同志带领120师以及晋绥的老百姓一起执行了毛主席的“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根据地就扩大了。他几次说这个“挤“字讲得好。父亲也常回忆在晋西南根据地的工作。那段时期是最困难的,因为他们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同时,还要对付阎锡山这个老滑头。我父亲曾经问毛主席:“如果阎锡山打我们怎么办?”毛主席回答:“他打你,你就打他嘛!”我父亲理解了,也灵活地执行了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所以在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的时候,成功地把大批革命有生力量保护了下来。这和一年以后的皖南事变结局成了鲜明对比。父亲几次说毛主席对他的回答是“要言不繁”。
许多曾在晋绥根据地和我父亲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常激动地和我们提起我父亲离开晋绥去东北以后,在晋绥发生的反右倾的那股风潮。我问父亲那是怎么回事?父亲说:有人在他离开了晋绥以后,批评他在晋绥的工作右倾,一些曾跟随他一起工作的同志和群众也受到打击。他在去东北的路上不断接到这些同志的报告。他一直带信给这些同志:稳住,不要有情绪,相信中央会正确处理。果然不久这股“左倾”风就被中央制止了。后来毛主席离开延安东渡黄河,进入了晋西北地区以后说:“开辟了这么大一片解放区,应该说成绩是主要的。”父亲说,这就是毛主席对他的工作的肯定和对那场争议的结论。后来,他在骑马去河北省西柏坡开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的路上遇到了这两个曾经“批判”过他的人,父亲首先下马,并首先做自我批评说:你们对我在晋绥工作中的一些批评是正确的,你们后来做了许多我当时想做而没来得及做的事。以后,他和这两个同志一直团结得很好。
也就是在抗战时期,他第一次和苏区来的军队干部有了直接接触。在晋西南时,他曾和115师的罗荣桓政委、在晋西北时他是和120师的关向应政委一起工作。父亲常回忆与这两个同志在一起工作的情形,对这两个同志非常钦佩,有很深的感情。我的弟弟炎炎和妹妹耿耿的名字都是为纪念关向应政委而起的。当关向应政委因肺病离职休养时,毛主席曾建议把我父亲从晋绥分局副书记提为晋绥分局书记。父亲对毛主席说:我没有关政委在军队中那样大的影响,还是做代书记吧。毛主席后来曾对人说:“林枫这人有自知之明。”
父亲出身于黑龙江一个富裕农民的家庭,以后又在北京、天津等地上学,在白区做地下工作。在山西的8年是他一生中物质条件最差的一段时间,但又是他一生中精神上最愉快的8年。父亲对山西人有偏爱。他说:“我是东北人,但我对山西的感情比对东北还深。”母亲也是这样。她坚持说:我的头骨比别的孩子硬,是因为她怀着我时吃了山西的小米子、红枣和酸菜。我的出生地兴县曾是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机关和八路军一二0师司令部的所在地。父亲说,那里的老百姓很穷,经常是全家人光着身子没有衣服穿。“你妈的一件竹布旗袍不知包了多少新娘子上轿。”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在那里组织老百姓大生产,人民的生活逐渐有了改善。至今,我们家保留着大生产时父亲给劳动模范张初元戴花的一张照片。我从小就看过这张照片,而且知道,张初元还是“劳武结合”的发起人。父亲曾在晋绥表扬和推广了张初元提出的“劳武结合”。1977年,父亲的追悼会后,一个农民模样的六七十岁的老人出现在我家门前,说他的名字叫张初元。我马上反应过来:“劳动模范张初元!”“文化大革命”后,父亲的名字从报纸上消失了。张初元心里一直惦记着。没想到11年后在报上再看到父亲的名字,竟是他去世的消息。张初元就从山西乡下赶到了北京,千辛万苦打听到了我们家,来看望母亲。我的心被深深地感动了。老人从千里之外匆匆赶来寻找和悼念30多年前给他戴光荣花的人,这得是多么深的感情哪!他对我们说:“那个时候的共产党是真的对老百姓好,和老百姓是一家人!”2006年5月,遵照母亲生前的嘱咐,我去兴县北坡村看望了60年前帮助我母亲带过我的白蝉儿。她当时还只是一个13岁的小姑娘,现在已经77岁了。但她能很快地说出当时晋绥分局很多干部的名字。她指着窑洞前的一块空地对我说:“当年你母亲就坐在这儿纺线线,我母亲就坐在那儿纺线线,我就抱着你站在这儿。”和我同去的小妹妹星星问她:“那时候,你怎么就帮助了我母亲呢?”想也没想她就说:“军民一家人嘛!”晋绥根据地和八路军一二0师就是依靠着这样一些老百姓的支持,成功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和其它根据地一起牵制了日本侵略军在华北地区的大部分兵力,把日本人挡在了黄河东面,成为革命圣地延安可靠的东大门。我们家从此也就和山西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记得,“文化大革命”前一到春节,我们家就响起了山西话,就充满了山西人的朗朗笑声。见到这些山西的老朋友,母亲和父亲总是非常高兴,特别愿意和他们一起回忆当年的生活。他们来的时候,也一定要问起“梅梅和胖双”。父亲在山西时的警卫员王玉珍叔叔是山西兴县的孤儿,15岁就跟上了八路军。父亲在那时的机要秘书韩乐风叔叔是山西洪洞县人,13岁就参加了革命,当机要员。他们都跟着父亲去了东北。我们从小跟着他们长大。据韩叔叔说,我是唯一能进他机要办公室的人,而且进了门就要上桌子,因为我当时只有两岁。对我们来说,他们比亲叔叔还亲。
我觉得,父亲和母亲传给我们的最宝贵的东西就是对普通群众和对劳动的尊敬和热爱。他们看到我们对服务人员态度不好,就会非常生气。上中学以后,我不再住校,他们就让我自己洗衣服,还给弟弟妹妹洗衣服,带小妹妹睡觉。上大学以后,母亲给我每月生活费20元,因为这是大学里学生的生活费标准。他们是要我们努力养成一种意识:我们是普通群众的一员。这么多年以后,回想这些,我才开始理解他们。因为他们深深地懂得:群众是历史真正的主人。
所以,这些年来,不论我们是在顺境还是逆境,父亲和母亲给我们灌输的这种“普通人”的意识、良好的劳动习惯和坦诚开朗的品格,使我们总是能交到朋友,找到支持。我想,这是父亲和母亲传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
1972年8月,父亲从秦城监狱出来时,母亲还关在当时设在中央政法干校的另一所监狱。父亲很想念母亲。一天晚上,他心脏病发作,医生给他采取抢救措施。他觉得自己活不过去了,就在深夜里把我叫醒,和我说了他想念母亲的心情。父亲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瞪得很大。我看着父亲,觉得全身心都被他出自肺腑的话语震动了。可喜的是,父亲终于活到了和母亲相见的那一天。1972年10月,在我们一再写信的请求下,母亲终于被放出来,在监护下住进了304医院。开始时,只许我们姐弟几个人探望,不许父亲和母亲见面。母亲还没有被放出来时,一个阿姨送给父亲几个很好的鸭梨。父亲舍不得吃,说要留给母亲。最后,几个鸭梨都干成了黑硬块,母亲还没放出来。有一次回家,我就把这几个干梨带回去,扔在了垃圾箱里。父亲马上就发现鸭梨不见了,一听说鸭梨被扔了,大发脾气,拒绝和我说话。我吓得赶紧骑上车,带着几个月的身孕,从阜成门飞速赶回和平里5号楼。幸好清理垃圾不及时,那几个干梨还在垃圾的顶端。我探身进去把梨拣了起来,送回到医院。父亲这才平了气。母亲出来以后,我把这几个干梨送给了母亲。母亲用缝被子的棉线织了个袋子,放进去,挂在桌旁,天天看着。我去304医院看母亲的时候,把父亲在病重时讲的关于她的话告诉了她。母亲总是一遍又一遍地要求我重复这些话。母亲去世的前几年,我每年都回北京看她。她每次都要求我坐在她身边并说:“你再把你爸爸和你说的那些话说一遍,他是这样说的吗?”我就耐心地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那些话。现在,母亲也走了,但她要求我重复那些话时期望的眼神还是会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1972年12月底,父亲和母亲都解除了监护。他们终于得以相见了。父亲给我的在1973年1月出生的女儿起名“庆庆”,两个庆,庆祝他们双双恢复自由。在阜外医院最后的两三年,正是双双的女儿林林和我的女儿庆庆三四岁最好玩的时候。父亲总是兴奋地等着她们的到来。从午觉醒来就早早地准备着,直到被她们折腾得筋疲力尽,不再答理她们为止。但等她们走了,他又会躺在那里回味她们说的每一句有趣的话。父亲后来身体越来越弱。尽管医生着急地催促他起来走路,他就是不肯起来,只有庆庆能把他拉起来。我那时候在贵州工作,常把庆庆放在北京。我的妹妹京京每天下午带着她去医院。我们家不分内外,我的儿女称我的父母为爷爷、奶奶。庆庆去了以后就“蛮横”地把爷爷从床上拉起来,拉着他到外面散步。父亲无可奈何,只好跟着她走。其他病人常会站在门口微笑地看着这一老一小在六病房的走廊里散步,纷纷招呼:“林老好!”看到庆庆有如此功效,父亲那时的主管医生王静大夫兴奋地对庆庆说:“你成了半个大夫了。我们给你一件医生的白大褂,每天就在这儿上班吧!”庆庆到现在仍然记得每次去看爷爷的时候,爷爷总是早就举起了手在等她的情景。天真的庆庆不能理解爷爷怎么会预先知道她来,还以为爷爷能掐会算。我知道,父亲每天都侧耳听着庆庆的小皮鞋在医院走廊里跑过的声音,所以早早就准备好了跟孙女握手。
后来,父亲的病情加重,1976年底,又患了脑血栓。尽管医生尽了一切努力,他还是在卧床11个月后去世了。
父亲去世以后,1979年7月和1984年7月,中国共产党分两次对父亲的入党时间和所谓历史问题做了澄清,为他恢复了名誉。
父亲没有活着见到这一天。他曾经期望过,等待过。1975年,我从贵州出差到北京,曾陪着他度过了几个等待的夜晚,但什么也没等到。失望之际,他站起来说:“哈!奇迹没有发生。”但这倔犟的老人执拗地相信,这一天会来到。他一再地说:“岳飞的案是孙子给翻的”,“盖棺不能论定”。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了,他兴奋地说:“我的结论有了!”为他的结论问题,有些老同志劝他马上给中央写信,他说:“中央出了这么大的事,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为我个人的事去打搅中央呢!”我想,父亲深深地懂得,只有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有了希望,他个人的结论才会有希望。
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我和我的妹妹、弟弟永远衷心感谢阜外医院的大夫、护士、职工们在“文革”中顶着那么大的政治压力让父亲的生命延长了5年,让他活着听到了孙子、孙女们的欢笑,使他活着看到了“四人帮”的倒台,让他活着看到了他所相信的群众取得的胜利。他没有完成的,我们——他的后代和他相信依靠的中国老百姓还会继续努力去完成。
作者:林梅梅,林枫长女,1942年生于山西兴县,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
本站编辑:林子
主办: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晋ICP备15001143号-1
Copyright Shanxi Jinsui Culture Education &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9号院国投财富广场4号楼313/314 邮编:100073 电话:010-63395639/63395661 邮箱:sxjs9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