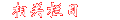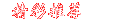
- 五卅运动中的父亲(06月10日)
- 云霞归来(06月10日)
- 北坡---我人生的第一个家(06月06日)
- 泥巴坨的传说(外一篇)(06月04日)
- 江姐革命引路人戴克宇去世(05月31日)
- 热血忠魂 (下)(05月30日)
- 热血忠魂 (中)(05月30日)
- 热血忠魂 (上)(05月30日)
- 晋绥艺术家--牛文(1)(05月29日)
- 忆我的父亲王其祥(05月28日)
怀念龚逢春同志
发布日期:2018-06-10 21:22 来源:龚逢春纪念文集 作者:安法孝
我认识龚逢春同志是在一九四零年下半年,当时他是晋西区党委的领导成员,我是晋西北行政公署的干部。我的职务和他的职务相差有几个层次,在工作上我和他接触很少,只知道他是陕西藉的老党员,陕甘苏区创始人之一,陕北红二十六军领导人之一。晋西区党委,晋西北新政权建立前,他是尚处在地下的晋西北区党委的领导成员。说起红二十六军来,我在察省民众抗日同盟军中任连指导员时,同营的另两名连指导员是从红二十六军调来的,是来支援的。联系起这事,我对逢春同志有一种特殊的钦佩之情。
我在逢春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是在一九五零年一月,川西区党委成立以后。逢春同志任区党委第三书记,分管农村工作。区党委成立后的头两年内,全中国进行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消灭封建制度,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列为四大任务,然后进行土地改革。逢春同志兼任川西农民协会临时委员会主任,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主要精力是抓减息、退押和土地改革工作。我当时虽在成都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川西行政公署工作,但在接管国民党政权以后,就根据川西区党委指示,从事退押和土改工作,直到一九五二年六、七月全地区(汉族地区)土改完成以后。这其间我一直在逢春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
一九五零年夏,川西土匪暴乱基本平息后,在开展减租退押前,逢春同志和区党委指定由区党委秘书长和我进行农村调查。我们带了两名新参加工作的本地干部到成都农村调查,我们访问了贫雇农,富裕中农,还访问了一户当时被认为政治上开明的中等地主,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川西地主阶级对农民(佃农)的土地剥削比北方还残酷,佃农(主要是贫农)除将一年粮食收获量的百分之七、八十作为地租缴给地主,佃农租种地主的土地时,还要向地主缴相当数量的押金。以后地租缴不足时,即从押金中扣除。佃农退还租地时,地主才给退还押金。实际上佃农退还租地就无地可种,祖祖辈辈靠租地生活,很少有退还租地的,所以押金实际上是不退还的。解放了,佃农按政府规定,少缴地租,地主不敢多收,佃农迫切要求是退还押金。
在地主阶级方面,则是另一种情况,既不承认他们出租土地是剥削农民,却认为地主养活了农民。我们和前述的那位据说政治上还开明,又有点文化的小地主分子谈话,他竟发表了一通谬论,他说,你们北方人不了解四川情况,在四川,卖地、少地的农民多,靠租佃地主的土地才能生活,他的结论是:农民是由地主养活的。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好,地主称佃农为“佃客”,好象湖南人称女婿为“堂客”一样,是以客人对待的,是亲戚关系。
我们回区党委机关后,把地主这种奇谈谬论向逢春同志汇报后,逢春同志即告区党委宣传部长,在《四川日报》上讨论农民与地主是谁养活谁的问题,成都市文艺工作者还编写了唱词,在群众会上演唱,驳倒了地主阶级的反动叫嚣,提高了农民兄弟的阶级觉悟。
李井泉同志和逢春同志认为退押是一场尖锐的斗争,是土地改革的前哨战,必须发动群众,认真进行,首先区党委和各地委组织工作组进行退押的试验,摸清押金情况,然后区党委制定政策和工作方法,由川西农民协会临时委员会发出号召,在川西汉族地区普遍执行,在经济上给封建势力以沉重打击。
对住在成都的地主的退押斗争则是在区党委即逢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开展的。
川西平原地区,即史称“天府之国”。土地肥沃,旱涝保收,成都市附近的成都、华阳、双流、温江、郫县、新繁、新都等七个县的大地主,大部分家住在成都市区内。他们剥削农民的押金当然很多。如果他们不首先清退押金,在小城镇、农村的中小地主就会持观望态度,拖延退押。地主中的恶霸、地痞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大部分已在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在政治上、经济上依法处理了。成都市是和平解放的城市,而住在市区内的大地主,不少人兼营工商业,个人成份有的是起义将领,官吏,有的是民主人士,开明士绅,有的是大学教授,各类学者。寺庙慈善机关也出租大量土地。不少是头面人物,是我党争取和团结的对象。根据老区土改的经验,如果这批人由农民群众揪回农村面对面的斗争,农民对顽抗、拒不全退押金者,在气愤之下,难免发生过火的斗争,增加对立情绪;如果由农民群众直接到市区的地主家中成群结队的住下来算帐、催押,党组织和农协会掌握不好,很可能破坏工商业和影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城市政策,而且农民并不完全了解地主有多少财产和退押资金。面对这种复杂的特殊情况,逢春同志在李井泉同志的支持下,经过几次讨论,最后确定,首先要突破住在成都市的大地主的退押问题。办法是以川西区农民协会的名义和七县农民协会商量,在成都成立川西农民协会领导下的七县农民协会驻蓉联合办事处(简称“七联”)以川西区党委副秘书长王定一同志任主任。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川西地下党领导人、与川西农民有联系的李维嘉同志和我为副主任。“七联”在市内各区设有催押工作组。“七联”采取走群众路线,调查摸底,发动群众清算押金数量,说理谈判与大小会面对面斗争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具体作法是各县农协分别把住在成都的地主应退的押金全算出来,成都市各区工作组摸清地主经济情况退押能力,然后区别对待,有的由各区工作组或“七联”分别向地主催要(对刘文辉将军等起义将领由逢春同志以农民协会名义与同情农民的民主人士一起和他们谈判退押)对凡是迟迟不退者和拒不退押者,由“七联”召集农民(佃户)代表来成都面对面的进行算帐斗争。“七联”还选择了若干个拒不退押的顽抗分子,发动农民代表有组织的进城,在人民公园举行了几次声势浩大的控诉大会,并给以罚款,责令其限期退还,对有的罪恶显著者还由人民法庭予以惩处。这对其他持观望态度的地主起了警告作用,加快了退押的速度,使退押的金额数量也得以增加。
经过调查研究,对确实退不够或无力退押的经“七联”批准,酌情减免。例如,巴金先生本家的寡妇,有祖上遗留下来的少量土地出租,押金和历年所收地租大部分作了五个子女的学费,两个子女是地下党员,另三个女儿在解放开始就参加了人民政府的工作,他们虽然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变卖衣物、家俱等财产,积极退押,仍退不够,她的女儿就到“七联”找到我,说明情况,请求减少,我们经过调查,核实情况后,就确定予以减少。如原藉陕西,住成都多年的严合荪先生,在成都是有名的藏书家和刻书家。“七联”把他应退的押金数目通知他,他到“七联”找到我,他说剥削农民的押金理应如数退还。无奈他家所收地租及押金都购买和刻印了古籍,家中实在没有钱退押,恳请将家中所藏书及刻书版目录交给我。“七联”就此事请示逢春同志,经他和区党委宣传部研究后,同意了他的请求,将这批古籍印书木版以捐赠形式移交给省立图书馆,押金免退。他的孙子现为四川大学副教授,前年谈及此事,他认为这样既保存了古籍,祖父又免遭斗争,党的政策是对头的。
经过半年左右的各种形式的斗争,地主退出了大批押金,“七联”将退抵押金的金、银珍宝及书、画文物,交有关部门以现金兑换收购,所收押金与各县农协协商,按比例统一分配给佃户。
经过退押斗争基本上满足了农民的要求,在经济上给地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对统战对象在政治上未给以大的伤害,保证了工商业,又保护了文物、寺庙。找认为是适合大城市反封建的正确的政策、方针和作法。逢春同志是参与研究制定这种决策的成员之一,而又是具体执行者。
在退押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问题。有些地主在成都市还拥有不少房产出赁,他们就乘退押机会,出卖房产,当时各机关缺办公室和职员宿舍,就纷纷购买,这样使得不少赁房居住的市民没有房子住了,他们不满的呼声,反映到区党委,区党委才及时下令,机关、团体不准买地主的房产,这事才平息了。减租退押工作结束后,紧接着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川西区土地集中,大地主多,一部分大地主与国民党政府官僚、地方军阀有直接联系,有的是土匪的后台,有的是“袍哥”头目、恶霸、地痞。例如,盘踞在大邑县安仁镇的刘文彩(刘文辉先生本家)土地(多为水田)有一万二千五百三十二亩(当时川西汉族地区每人平均土地只有一亩多)分布在十一个县,他家拥有看家的武装,私设公堂,还有水牢,与军阀有联系,称霸一方,地主阶级中还有“二地主”即向大地主租赁土地后,再转手租出去。有的佃户成分又是富农即向地主租赁土地后雇人耕种。还有一些出租少量土地的小地主即拥有少量土地,自家无劳动力耕种,而出租出去地租仅够维持生活,土改时划分为小土地出赁者,(按富农对待)而大批农民贫无立锥之地,靠租种土地和作长、短工维持生活,农村阶级关系和土地问题非常复杂。根据中央指示,顺利地正确地完成土改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区党委还是先进行土改实验,摸清基本情况后,根据中央、西南局颁布的政策规定,结合川西区实际情况,制定了周密的政策规定、工作方法,在全汉族地区分期分批的进行。
我是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中旬带领有民主人士参加的工作队到夹江县山区、丘陵地区两个乡土改试验,然后带领有大批解放后参加工作在“革命大学”训练过的青年知识分子,以老区来的干部为骨干,组成工作团,在广汉、德阳、什邡三县(以后又加了半个金堂县)在区党委逢春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土改。
这次土改,中央、西南局有完备的政策和指示。井泉同志、逢春同志又有晋绥老区土改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根据川西实际情况,指导具体。经过一年半多的时间,正确地胜利地搬倒了封建制度这座大山。逢春同志作为分管土改领导,川西区土改委员会主任,对全区土改运动竭尽全力,作了具体的及时的指导。特别注意对大小地主的区别对待。
逢春同志在区党委办公厅内设立了一个由有老区土改经验的干部作为骨干的精干的“参谋”班子,经常下乡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及时向他汇报,并编写了一份《土改通讯》,及时传播土改经验,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逢春同志特别注意第一期土改经验,我率领的第一期土改工作团,团部设在广汉中内乡(该乡近年来发掘出来的古蜀文化遗址,即三星堆所在乡)一所大古庙里。川西区第一期土改,中央派有十几名京津的民主人士参加,其中参加我团的有天津的著名作家、翻译家李霁野先生,天津大绅士某人,北京清华大学的著名教授陆志伟先生,成都也有几名民主人士参加;逢春同志风尘仆仆地特来我团住了几天,住在我原来住的一间潮湿的小破殿里,他访问了土改积极分子,乡村农协主席,听取我们的汇报,并和住团部的民主人士座谈征求他们对土改政策和作法的意见。并向民主人士和我们谈过去苏区土改、解放战争时期的老区土改情况,土改后头一两年,农业生产有所下降,原因是富农、富裕中农生产不积极了。他问我们这次土改后是否还会发生这种现象。有科学头脑的民主人士说,不会的,这次土改,中立富农的政策执行的好,又特别注意不侵犯中农利益;富农、中农生产资料齐全,现在还是农业生产的主力,而贫雇农,分得了土地,积极性高,因此,生产不会下降。逢春同志听了,很满意点头称是。事实上,土改结束后,农村立即掀起了生产热潮。土改结束不久,一九五二年九月一日,四川境内的四个行政区合并为四川省。省委成立后,逢春调任西南局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兼西南局党校副校长、党委书记。西南局撤销后,西南局党校改为由中央直接领导的第七中级党校,一九五八年与四川省委党校合并为新的四川省委党校,逢春同志一直任校长、党委书记,并当选为省政协副主席。逢春同志在晋绥边区时就兼任过晋绥分局的党校校长和分局组织部长,他有培养干部的丰富经验,又德高望重,是最好的为人师表的领导人。党校由省委直接领导,具体事情由组织部联系解决,我当时是省委组织部负责人之一,我在处理具体事务时,总是视他为领导,很尊重他。他也非常尊重组织部的意见,由此可以显示他坚强的党性和高尚的风格。两校有部分干部因性格不尽相同,来源于几个地区,曾发生过一些不团结、工作不协调的现象,逢春同志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循循善诱作了有效的思想工作,为广大干部所钦佩爱戴。
一九六三年,逢春同志被调任为中央党校副校长,李井泉同志为他举行了送别宴会,会上李井泉同志对他说:“老龚呀,你身体不好,担子重了,如力不从心,欢迎你返回四川工作。”逢春同志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四川。
“ 文革”初期,他在中央党校被造反派批斗,消息传到四川,四川省委党校造反派中有些人曾酝酿把逢春同志揪回四川批斗,多数正直的干部说:“我们批斗这位老领导的什么问题呢?”此后他在四川幸免于难。
一九七三年,我被“解放”后第一次赴京开高教会议,获知逢春同志身心遭受摧残,已经住进了医院里了。当时他尚未被“解放”,我急忙去医院探望和慰问他,劫后重相见,他自然很高兴,只见他清瘦多了,他从病床上勉强坐起来和我紧紧握手不放。他平日不善言谈少言慢语,这次竟幽默地对我说:“真是无奇不有,他们(指造反派康生等人)竟然说我是国民党员,这个国民党党员竟然当起了共产党中央党校的副校长!”他说着便哈哈大笑起来。一直在医院护理他的夫人姜宝箴同志背着他对我说:“老龚病重,我已催促中央党校很快给他作结论”。1978年,中央党校宣布了对他彻底平反的决定,恢复了他革命一生的本来面目。我们——他的老部下,自然很高兴。我离京前再去看望他,只见他并不兴奋,康生和造反派对他的迫害,本来就是无中生有,他是对党和国家的命运忧虑。
1974年,我调江津地委工作。1976年冬,我再次到北京开会,特意给他带了一小筐他喜欢吃的江津广柑去看望他,只见他趟在床上,噙着眼泪注视我好久,像是说: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了。我一阵心酸。他慢腾腾地对我讲,前几天,来了一位和他在晋绥边区工作过的老部下看望他,这位同志在“文革”中陷入派性。他们谈话时,对“文革”的是非争论起来了,他们没有共同语言。这位同志说,逢春同志是老脑筋,思想赶不上时代了,逢春同志很气愤。这时他向我提及此事说:“人家赶上时代了,我还是老脑筋,落伍了,他竟来教训我。”言下仍不胜愤慨。
龚逢春是在看到“四人帮”垮台,党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同志实际上已掌握了中央领导权后逝世的,他生前忧虑的党和国家的命运,已经得救了。大约他瞑目了,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人民的解放,坚持不懈地,艰苦奋斗了半个世纪,他可以休息了。
龚逢春德高望重,高风亮节,永远是我们尊敬和怀念的!
1990年8月
作者:前任四川省委常委、组织部长
中共四川省委顾问委员会常委
资料来源:《龚逢春纪念文集》
本站编辑 林子
主办: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晋ICP备15001143号-1
Copyright Shanxi Jinsui Culture Education &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9号院国投财富广场4号楼313/314 邮编:100073 电话:010-63395639/63395661 邮箱:sxjs9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