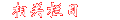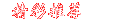
- 晋绥儿女携手加多宝集团走进吕梁市捐资助学(08月04日)
- 关向应与贺龙的革命情谊(07月06日)
- 关向应:忠心耿耿为党为国(07月06日)
- 党的生日---怀念向应(07月01日)
- 信仰的味道:陈望道首译《共产党宣言》(06月23日)
- 初到偏关(清明祭)(06月23日)
- 2016年“加多宝·学子情”爱心助学行动在京启动(06月22日)
- 共同携手---把爱心助学带进老区(06月22日)
- 基金会通过了2015年度检查(06月22日)
- 光辉历程--《共产党宣言》首译本保存记(06月22日)
《我的回忆》文革(五)
发布日期:2016-06-28 14:51 来源:《我的回忆》
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入人高潮时,大字报铺天盖地。大小批判会过后的一段时候,有一红卫兵战斗队把我叫到他们的队部说:“你从今天起,在这里认真学习报刊上有关‘文革’的论著。”从那天开始,我准时去,按时走,一连好些天,实际上给这个战斗队看家,他们每天忙着出去,谁也没有我,等于避难。
过了些天,突然通知我到大门口,然后去门头沟接受批斗。我一听,知道是1965年冬,我亲手处理一件谋杀案,文革中造反派强制对该案平反后,把两个嫌疑人:年轻炊事员从劳动场所要回来,在他们村里批斗学院领导人。事因是一个在北京的外国人,被歹徒杀害,中央指示由公安部发出文件,凡有外籍人的部门,有行凶嫌疑者,按情节送边疆劳动。当时我院有外籍外语教师。本院的这件事,是一位老炊事员秘密告知我的。他亲眼看见上述两个炊事员 晚饭后,偷偷磨好刀子放在床下的鞋里。他们还告诉老炊事员:“今晚不要再睡错了床。”老炊事员并告知我:“他俩平时对炊事班长杨德忠很不满。”我听说后,马上令保卫科科长李云兴带着科员张昆仑赶快去查出磨快的刀子,于是我决定把这两个炊事员隔离起来,经公安部审批送新疆劳动。话说回来,通知我去受批斗,当我赶忙走到《毛主席去安源》的画像前,对面迎来两个红卫兵拦着我说:“你的表现还可以,不用去了。”这样,据说那次斗的挺凶的大会,我幸免受罚。后来有人告诉我,当时管后勤的副院长受批斗后说:“案子是冯文耀办的,挨斗时他溜了。”造反派把两个炊事员从劳动地方要回来前,曾开中型批斗会斗过我。会上我讲了事实和原因、根据和处理过程,没有认错,背后遭到一造反派的脚踢,罚跪五六小时。我回家走路不到百米远,但途中休息了四次才半爬半走地回到了家里。
1966年冬初,红卫兵“丛中笑”战斗队贴出一张大字报,要吸收我参加战斗队。我立即去向他们声明:“我现在是接受批评教育的,请原谅我的要求,不吸收我为好。”他们十几个人听我申述后,互相观望了一会儿,有的说:“可以,不过你以后随时来这里看看我们收集的各类论文,抄印的大字报。”我虽然答应了,但从未主动去阅览过。
寒冷的一天,我被勒令去部里接受陪斗,还给我头上戴着“刽子手”的纸高帽子。斗争大会开始前,把局长们以及于苇和我,先在院子里游斗,身上前后粘贴着大标语,走起来作出飞机式的样子,然后都进入红楼礼堂,陪斗的人在台下前面排队,低着头。斗争会开了些时,台上大喊一声:“冯文耀滚上台来!”这时,走来一个红卫兵,领着我往台上“滚”,到台阶下,说一声“你站一下”。说完他当即上台对主持会议的学 院红卫兵领导人说:“冯文耀发高烧。”主持人一摆手说:“叫他回去吧!”没有滚字。这样,我又(“溜了一次”)躲过一劫。当我走出礼堂大门后,又一个红卫兵追上来说:“等一等”!结果,他把我身上粘贴的“反革命分子,刽子手”等大字标语撕掉了。小将们对我采取的这些“明批斗,暗保护”的种种举措,我至今回想起来仍感不已。
1967年秋的一天,教职工三、四十人召开了一次帮我认识错误的会议,政治部副主任杨明奎、教务处长兼法德系主任、党支书黄杏文,也都是院党委委员,一年前调进来的,还有各系处的干部、工人。批评者都平心静气,几乎都规劝我正确对待群众意见。有的造反派大概是闻风而去。散会时,有一人气愤地说:“你们是假批真保。”大家并没有批评,而是提醒我不要得罪造反派。当时心里十分感激这次会议的召集者。
在这次会议之之前,有几个红卫兵战斗队,其中有“丛中笑”,联合贴出《保冯声明》的大字报,主要说“冯文耀是人民内部矛盾,虽有错误,但不是不可救药。”,大字报里声明不同意按敌我矛盾批斗,应善意地批评帮助。我一看到标题,没敢读正文,便马上回家了。当时想,要是造反派有质问,要我回答,在当时的情况下很难开口。但很快有的同志给我抄写了一份,使我知道了全部内容。联系前述的几件事,我深知小将们中有不少人是能分清是非,并是有政治责任感的。
约在1968年末,于苇的儿子于晓星突然跑到我家说:“了不得了,外面大字报上说,舍得一身剐,敢把冯叔叔拉下马”。家里人听了出去一看,第二句是“敢把冯文耀扶上马。”原来是看错两个字,把“扶上”自然想成“拉下”。因为毛泽东的名言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嘛。我到院里,看到好多人围着看大字报,近前看到标题和后面署名中有遵义兵团等红卫兵战斗队后赶快回避往家走,又闭门不出,免得有人当众出难题。后来知道这张大字报的内容:要求按照毛泽东关于建立革委会中“三结合”的规定执行,强调须有革命干部的代表进入领导班子。当时,在全国掀起“三结合”以抑制造反派一派掌权。
过了几天,批判我的大字报又多起来了,特别是对1959年我执笔写的《调查报告》,天天连篇累牍,几乎贴满了文革初我组织搭起长达十米的席棚。这篇最长的大字报的贴出,对我来说,正是经常出来仔细阅读并与大家见面的时候。我看得很仔细。看完第一遍,我再去看时带着纸笔,把《调查报告》原文抄写下来,保存到现在。这篇批判的大字报所以很长,人家是照着《调查报告》逐字逐句地详细批判的。因此我看得很仔细很认真,可惜未将大字报原文摘来。批判的结论仍然指我走富农路线,一贯右倾,反对基层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等等。大字报笔者也许不了解1961年以来党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政策的颁布和修改的文件。如果文革时允许被批斗者说话的话,就可以向其解释。该笔者前些年从天津来京出差,还上我家一次,临走时握住手问:“你恨不恨我?”我答:“要感谢你……从我参加革命到文革开始前,工作中的对与错,没有认真全面总结,经过你和同学们的帮助,我的头脑清醒多了”。
在阅读对我的大字报时,也看了不少其他方面的大字报,其中有我在前文中所说关于盘慧灵被害以及其家财务被坏人占为己的事,也有关于陈四维教授的钱款被个别造反分子“借”走不还的事,同时揭发里英璞包庇上述“革命”+ 贪财的造反人物。
文革开始不久,调查部上报中央并经批准,本院的“运动”由北京市领导。但到 1969年春,情况又有了变化。
1969年5月4日,北京市革委会文教组关于国际关系学院的文革运动报告,先由市革委会负责人吴德、谢富治等把报告送康生、周总理,总理当即批示:“先送调查部陈(注:军代表陈兴华)罗,并提出意见。调查部为何插手?部的军代表不要参加,自惹麻烦,割断关系。”时为军代表之一的朱导良和时为部长的罗青长作了签名检讨:“接受总理对我部为何插手国关文革自惹麻烦的批评,坚决拥护总理对我部与该院割断关系的指示,接受教训,改正错误。”总理看到朱、罗在文件上的检讨后批语是“解铃还需系铃人”。5月5日,北京市文革小组报告内容主要是:
“四月以来,原一派正式申明,不承认院革委会,重新拉起‘遵义兵团’,因此‘九大’闭幕和‘五一’晚会等重大活动均不能联合参加。”
“三月,曾因对原第二书记冯文耀的看法产生分歧,又分成两派,矛盾渐展,几经反复,终未解决。”
“军宣队进校后,对‘地下黑司令部’匆忙表态,压了‘遵义兵团’……对缺点错误作了公总结检查,准备调整院革委会,形势逐渐好转。”
“意见:
一、革委会是合法的,做群众工作……
二、建议该院文革由调查部领导。”
从北京市革委会文教组的报告中,人们才知道当时背后又有大势力插进手来,压了“遵义兵团”,可是小将们仍坚持斗争,使北京市革委会文教小组无能为力,写报告建议仍由调查部领导。周恩来总理看到报告,批评了部里,使真相大白。
1969年秋末的一天,革委会派人把我叫去。我一进会议室,看见人已坐满。我刚坐下,驻院军宣队政委、院委会主任、整党领导小组组长王玖祯宣布:“上级决定冯文耀同志为院革委会副主任,整党领导小组成员”。会议没有讨论任何问题就散会了。是哪个上级决定的,王玖祯未讲,我也没问,更没有想。
我被结合进院革委会后,有人贴出大字报提出“冯文耀还没有恢复党员的组织生活,怎能担任院整党领导小组成员?”这一问题提得令人应该深思。我至今也不知道是何组织何时决定停止我的党员组织生活的,在什么条件下,经审查合格才能恢复党的生活?在结合我时直至后来谁也没有给我办恢复的手续,但结合后,一直担任整党领导小组成员。就这一点看.文革中违背党章的情形已是屡见不鲜了。
1970年3月,驻中央调查部的军代表陈兴华、部长罗青长来学院,在院革委会全体议上由陈宣布:“国际关系学院为撤销单位,全院师生员工597人,全部交河北省处理。”我提了两条建议,首先说建校困难,师资、图书都是从无到有,应保存力量,我们不要,总有一天国家会用的,一、现在图书有七万册,其中有不少宝贵的工具书,文革开始前夕,我们托驻外使领馆帮购进大小牛津字典两大箱,还没有启封,应+成立图书移交小组。陈兴华生气地质问:“你这是什么意思?”他大概以为我借口参加移交工作不到农村去劳动。我立刻回答:“请放心,我第一个下放劳动,绝不参加移交工作。”我的另一个建议是:“老院长患了心脏病,不能劳动,请另做安排。”陈马上说:“甘(指甘霖)院长的问题我已有考虑。”我立刻纠正说:“我建议不能下放的是于苇同志”。他不吭声了。
到河北饶阳插队落户的实际上不是597人,其中工人留在北京分配;知识分子和干部下放到河北接受贫下中农;老年教师被强制退休到京郊延庆县农村居住;六三、六四两届本科生由北京军区分配除河北外的华北地区;五届本科生和剩下的教职员包括部分家属一起迁走。
(本站来源:冯文耀著 《我的回忆》 本站编辑:姚文君》
主办: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晋ICP备15001143号-1
Copyright Shanxi Jinsui Culture Education &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9号院国投财富广场4号楼313/314 邮编:100073 电话:010-63395639/63395661 邮箱:sxjs9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