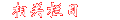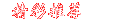
- 晋绥儿女携手加多宝集团走进吕梁市捐资助学(08月04日)
- 关向应与贺龙的革命情谊(07月06日)
- 关向应:忠心耿耿为党为国(07月06日)
- 党的生日---怀念向应(07月01日)
- 信仰的味道:陈望道首译《共产党宣言》(06月23日)
- 初到偏关(清明祭)(06月23日)
- 2016年“加多宝·学子情”爱心助学行动在京启动(06月22日)
- 共同携手---把爱心助学带进老区(06月22日)
- 基金会通过了2015年度检查(06月22日)
- 光辉历程--《共产党宣言》首译本保存记(06月22日)
《我的回忆》文革(三)
发布日期:2016-06-27 12:05 来源:《我的回忆》
本院师生中造反的极左顽固分子一直占少数,其中教师中只有个别人,职工中不到百分之二。政治部包括马列教师大概五分之一,其中包括组织处处长里英璞(兼院长办公室主任);总务处十分之一,这个处工人(包括炊事员)多事处和教务处各有半数。全院三个系,每个系有政治指导员三人,在九人中只有一个人,各系党政正副领导九人中有两三个。总共八十多人吧,所谓造反的有十四、五人。主要特点是:一、到校工作很短,其中里英璞及其妻(日语系党支部副书记)调来才一年;二是系处级干部多,几乎占了一半;三是工人中极少造反,几乎无一造反者。
学院原来有很大一部分师生和教职工,是不同意造反派的观点和行为的,但在当时那样何去何从的严峻政治形势下,有一部分人转向造反派,对院党委来了个反戈一击,甚至有的那股蛮干劲比起老造反派来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过些时候,有些人总觉得造好人的反不对,又站过来保护党委中的绝大多数人和他们的老师。从此以后直到 1970年初学院被撤销,所谓保守派的人数始终是多数,有人估计约占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但掌权的是以里英璞为主的造反派,里当时还是院党委委员,也是党委委员中唯一的造反派。1966年8月5日召开了著名的“八·五”辩论大会。当时党中央常委李富春同志莅临讲话,号召大家联合起来搞好文革,要文斗不要武斗,也不要相互斗争。学生中的一个造反派上台大声说:“这是和稀泥,”富春同志当即毫不退让地说:“这不是和稀泥!我们党历来主张人民内部要团结。”老人家的声音很洪亮,博得广大师生员工的热烈鼓掌。有的造反派当面以无聊的语言诬蔑孔原同志,胡说什么“孔圆、孔方、孔三角。”另一派同学和在场的十九中、一零一中的学生几乎齐声反击说:“不许辱骂孔伯伯!”这时,冯铉副部长说了一句:“大家应该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里英璞以为他造了院党委的反还不过瘾,上前以教训的口吻道:“你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这时有几位同学赶快站在冯铉周围,以保护这位副部长的安全,有的同学反问里英璞:“你胡说八道的资格是谁给的?”质问的他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在大会上,有一个造反派学生突然飞奔上台,高举笔记本一册,质问:“这是谁发的,想干什么?”我一看是日、西系学生,马上想起一件事,即在运动之初,院党委召开各系支部正副书记会,布置发动学生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有关工作。会议结束时,我给每个系发了笔记本。里英璞的妻子是当时的日西系党支部副书记,她很可能想是以笔记本一事,妄图证明党委要镇压造反派。我立即上台申明:“笔记本是我在支书会议上发的,请各系副支书随时记录每个人的言行,以后整理材料时避免差错。”我回答完后,全场鸦雀无声。过了一会儿,另一个造反的学生说:“这是你想秋后算帐。”一个保守派的学生说:“这是为了不冤枉好人,有什么不对?”这位同学的反驳,比我的回答更针锋相对,至此,再没有人发言了。
“文革”中有相当一段时间各校学生包括中小学学生开展了大串联,他们在串联中搞了些什么活动,我至今一无所知。外地学生来京串联,是接受毛泽东检阅,为此,各机关、学校要接待好这一批批上百万学生的串联队伍。当时本院造反派让我为外地串联来院里的红卫兵端水送饭,清扫宿舍,我都精心照办了,本院学生大部分也分批外出串联。但造反派中骨干人物守着已得的“江山”没有出去。
造反派强占了播音室,在院里安装了高音喇叭,不管什么么时候,发通知下命令,都用它发出。有时为了审问于苇和我,在喇叭上发出“冯文耀滚上教学楼五号房来!”我们也就老老实实地“滚”上去接受了不少次的“教育”。
同学分批外出串联,也分先后返校。但是那些所谓保守派或逍遥派的同学一旦回到学校,高音喇叭上就播出“某某某的丧钟敲响了”,以示造反派胜利,“保守派”失败。同时,还高声命令学院未造反的各级领导到《毛主席去安源》的画像前集中,给我们俩正副书记戴上纸高帽,腰弯九十度,手拿铜锣还得用力敲打,让串联回校的“保守派”看看造反派多么威风。有个同学名叫陈继成,串联回广州,贴了揭发其父的大字报;回校后,大概后悔了,精神有些失常。他平时背一支自造木头步枪。一天,突然传出陈继成从教学主楼顶层跳下身亡的消息。真令人可惜可叹!一个青年学子,要不是文化大革命那场风暴,哪会发生这类痛心的事。事发后,他的父亲,时为广东省委组织部长,从广州来京,悲痛地料理了后事。
文革中,父母受迫害,往往子女也受株连。比如,林枫:中央党校校长)的女儿林耿耿、伍修权(外交部副部长)的女儿伍延力,两个都是国关的学生,父母挨整了,她俩也被随意批斗,甚至党籍都难保。在军宣队支左驻院掌权后,与造反当上革委会副主任的里英璞等,一直主张开除两个女生的党籍。
里英璞任院革委会副主任不久,突然宣布了整党三人小组。他是组长,组员有预备党员英语系本科生张新祥,日西系本科生非党员许金生。整党小组一经宣布,立即引起了党内外群众坚决反对,甚至连造反的人也感到该小组名不正言不顺。没有想到里英璞这个当过组织处长的人,竟然使出如此违背党内基本组织常识的愚蠢一招,给造反派带来了被动。大概是因为无人赞成和众人坚决反对,不到二三小时,整党领导小组的名单不见了,他们也再未提整党的事。
这里提前叙述1970 年 1月,学院被撤销,下放河北饶阳县后,对林耿耿、伍延力党籍处理的经过。当时的院革委会主任、整党领导小组组长是驻院军宣队政委王玖祯,革委会副主任是里英璞、军宣队队长、工宣队政委,也都是整党小组成员。约在1969年10月间,也许是11月,我被结合为院革委会副主任,整党领导小组成员。一日,王玖祯主持召开整党领导小组会议,讨论决定林耿耿、伍延力的党籍,工宣队政委到会晚,一进门说:“我得修鞋去”,说完走了。林、伍二人未到会。王提出开除林、伍二人的党籍,理由是包庇她们父亲的罪行。我马上反驳说:“林枫、伍修权二同志的问题还没有定性,即使问题很严重,说她们所谓包庇的事实也没有证据。”他们不顾我的意见,马上举手表决,除我一票反对,林耿耿、伍延力被决定开除党籍。工宣队政委在会后告诉我,他是有意不参加会议,我说:“我意识到了”。林耿耿得知后,马上离开饶阳。伍延力告诉我,林去反映问题,并说:“我俩坚决拒绝这一决定。”我说:“完全对,一定不会照他们的决定办的。”过些年后,我又见到伍延力,她说问题都解决了,她俩都还是党员。
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四大”被宣称是一场比“五四”运动、延安整风更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但实际上,全部事实和整个过程,是以民主之名,反民主为实,根本没有民主。许多人没自由。“四大”是只许少数人“鸣”,少数人“放”,少数骂多数叫做“辩”,少数可以在大字报上侮辱人,甚至罪名,陷害无辜。民主与法制遭到践踏,思想道德破坏无遗。极端个人主义大发展,无政府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恶性大泛滥,对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空前大摧残,工农业经济、包括交通运输等,要不是周恩来总理忍辱负重,殚精竭虑,力撑苦局,千方百计保护党和国家领导干部和人才,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话,那损失会更加惨重。
(本文来源:冯文耀著《我的回忆》 本文编辑:姚文君)
主办: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晋ICP备15001143号-1
Copyright Shanxi Jinsui Culture Education &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9号院国投财富广场4号楼313/314 邮编:100073 电话:010-63395639/63395661 邮箱:sxjs93@163.com